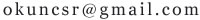第1个回答 2010-12-07
巴金的故事一:钱,是用来买书的
汽车库、储藏室、阁楼上、楼道口、阳台前、厕所间、客厅里、卧房内……在巴金偌大的寓所内,曾经到处是书。巴金爱书,在文化圈内是出了名的。他的藏书之多,在当代文人中,恐怕无人可比。
藏书多,自然在于书买得多。
巴金胞弟李济生曾谈起四哥爱书、买书的情况:“说到他最喜爱的东西,还是书。这一兴趣从小到老没有变。在法国过着穷学生的清苦生活时,省吃俭用余下来的钱,就是买自己喜爱的书。有了稿费收入,个人生活不愁,自然更要买书。‘1·28’日本侵略军的炮火毁去了他的住处,收藏的书也随之毁了。习惯已成,兴趣所在,书慢慢地又积累起来。去日本小住1年,就买了许多英日文版书带回来。有的名家作品他会不遗余力地搜集各种文字的译本。住屋几乎全放满了书。解放后搬了家,房子宽敞了,书架、书橱也随之增多增大。书房内四壁皆书,客厅内也顺墙壁一溜立上4只大书橱,连走廊上、过道上也放有书橱。一句话,无处不是书了。”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巴金一家生活已很拮据,只剩下57元银元。萧珊从菜场买来价廉的小黄鱼和青菜,用盐腌起来,晾干。每天取出一点,就算全家有了荤腥蔬菜吃了。这两只菜,竟然支撑了全家半年的伙食。
一天傍晚,楼梯传来巴金沉重的脚步。萧珊和养子绍弥迎了上去,只见他提着两大包刚买的书,气喘喘的。萧珊问道:“又买书了?”“嗯,当然要买书了。”巴金回答道。从来就十分尊重,也什么都依着巴金的萧珊,这时说了一句:“家里已经没有什么钱了。”巴金问也不问家里到底还有多少钱,日子能不能过下去,就说道:“钱,就是用来买书的。都不买书,写书人怎么活法?”
第2天,他又带着孩子们去逛书店了。
巴金买书真的没商量。
在现存的300多封巴金与萧珊的通信中,有不少内容是关于寄钱买书的。1949年9月20日巴金书信萧珊:“昨天刚寄出一信,今早又收到你的信了。我还没有到开明去拿钱,过两天我会去拿的。其实我自己也不需要多少钱,不过来北平一趟总得买点东西带回去送人,我自己也想买几本书。”从中可以看出,巴金这时在北京,准备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巴金已寄信嘱萧珊汇钱来,等不及又发信回去。
这是一封巴金写于1956年6月23日的信,其中有这样一段:“这次买书较少,已寄了几包回去,大概还有几包。”已寄了几包回去,还有几包,这还是买得少的,那么多的呢?可以想像,巴金买书有多“狠”。这次寄信的地点也是在北京。据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巴金去北京,没有一次不买书回来的。琉璃厂、王府井,都是巴金必去的地方。
巴金的故事二:称自己的作品百分之五十是废品
《巴金全集》26卷,700来万字。这是巴金献给人类的一笔巨大财富。
文人多自尊,多轻狂,多自以为是。世上少有赞叹别人的文人,更鲜有批评自己的文人。所谓“文人相轻”,不仅有道理,而且是一个普遍现象。
巴金却说自己“不”。这个“不”,不是他在《随想录》中对自己灵魂的拷问,而是对自己的文学成就,文学生命:他说,他的作品,百分之五十是废品。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人民文学出版社拟出版《巴金全集》。起初,巴金不同意。编辑王仰晨几次来沪做说服工作,被王仰晨的热情和决心打动,一年后巴金终于同意了。
巴金为何不同意出版他的《全集》?巴金说,编印《全集》是对自己的一次惩罚。因为,他认为,他的作品百分之五十不合格,是废品。
巴金是无情的。他说,第4卷中的《死去的太阳》,是一篇幼稚之作,第5卷中的《利娜》,严格地说还不是“创作”。他认为《砂丁》和《雪》都是失败之作。这两篇小说,写于30年代初,以矿工生活为题材。他虽然在长兴煤矿住过一个星期,但是对矿工的生活,了解的还只是皮毛。因此,编造的成分很大。尽管如此,当时统治者很害怕这两篇小说,发行不久就遭到查禁。《雪》的原名叫《萌芽》,重印时改为《雪》。
巴金是严厉的。在读者中广为流传的《爱情三部曲》,他也说是不成功之作。在《巴金全集》第6卷“代跋”中,巴金开篇就写道:“《爱情三部曲》也不是成功之作。关于这三卷书我讲过不少夸张的话,甚至有些装腔作势。我说我喜欢它们,1936年我写《总序》的时候,我的感情是真诚的。今天我重读小说中某些篇章,我的心仍然不平静,不过我不像从前那样的喜欢它们了,我看到了一些编造的东西。有人批评我写革命‘上无领导、下无群众’,说这样的革命是空想,永远‘革’不起来。说得对!我没有一点革命的经验。也可以说,我没有写革命的‘本钱’。我只是想为一些熟人画像,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使我感动的发光的东西。我拿着画笔感到毫无办法时,就求助于想象,求助于编造,企图给人物增添光彩,结果却毫无所得。”
巴金是苛刻的。他还说《火》是失败之作。《火》也是三部曲。说它是失败之作,巴金多次讲过。在编选《巴金选集》时,也没有把它们收进去。巴金说:“我不掩盖自己的缺点。但写一个短篇,不一定会暴露我的缺点。写中篇、长篇那就不同了,离不了生活,少不了对生活的感受。生活不够,感受不深,只好避实就虚,因此写出了肤浅的作品。”关于《火》,巴金还说:“三卷《火》中我写了两位熟人……但是我应该承认跟我这样熟的两个人我都没有写好……除了刚才说的‘避实就虚’外,我还有一个毛病,我做文章一贯信笔写去,不是想好才写。我没有计划,没有蓝图,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所以我不是艺术家,也不是文学家,更不是什么大师。我只是用笔做武器,靠作品生活,在作品中进行战斗。我经常战败,倒下去,又爬起来,继续战斗。”
巴金是彻底的。他觉得,他在一些文章中写了自己不想说的话,写了自己不理解的事情。在一些作品里,他还写了许多不切实际的豪言壮语,与读者的距离越来越远。他的百分之五十废品的观点,自然不被人们认同。编辑王仰晨首先在给巴金的信中表达了异议。巴金回信道:“说到废品你不同意,你以为我谦虚。你不同意我那百分之五十的废品的看法。但是,重读过去的文章,我绝不能宽恕自己。有人责问我为什么把自己搞得这样痛苦,正因为我无法使笔下的豪言壮举成为现实。”
巴金是理智的。他清晰地看到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化。所以,他说:“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青年把我当作他们的朋友……在十八九岁的日子,热情像一锅煮沸的油,谁也愿意贡献出自己宝贵的血。我写了一本又一本的书,一次又一次地送到年轻读者手中。我感觉到我们之间的友谊在加深。但是二十年后,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青年就不理解我了。我感到寂寞、孤独,因为我老了,我的书也老了,无论怎样修饰、加工,也不能给它们增加多少生命。你不用替我惋惜,不是他们离开我,是我离开了他们。我的时代可能已经过去。我理解了自己,就不会感动遗憾,也希望读者理解我。”
一个睿智的人,一个真诚的人,一个可敬的人——巴金。
巴金的故事三:出书献给读者是莫大的快乐
中国文学和中国出版史上,留有值得大书的一页: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这个由吴朗西、巴金等人创办的小小的同仁出版社,却为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从1935年创办到1954年公私合营,出版社出版发行了28种丛刊、专集、选集,计有226部作品。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书,是经总编辑巴金的手编排发印的。
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当年的老编辑、巴金胞弟李济生整理的图书出版目录中,我们看到了一长串在中国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作品:《故事新编》、《骆驼祥子》、《边陲线上》、《憩园》、《第三代》、《淘金记》、《前夕》、《八骏图》、《路》、《团圆》、《南行记》、《运河》、《饭余集》、《雷雨》、《日出》……长篇、中篇、短篇、散文、诗歌、戏剧……涵盖各个文学门类。
鲁迅、茅盾、老舍、巴金、沈从文、曹禺、汪曾祺、李健吾、靳以、艾芜、沙汀、郑振铎、黄源、穆旦、何其芳、唐弢、萧乾、李广田、师陀、黄棠、王西彦、黎烈文、柯灵、鲁彦、方令儒、芦焚、张天翼、王统照、肖军、胡风、罗洪、吴组缃、丽尼、欧阳山、陈荒煤、刘白羽、艾青、卞之琳、臧克家、端木蕻良、陈白尘、曹葆华、冯至……86位作家, 在中国文学史上,灿若星际。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文坛流派纷呈,社团众多,阵营分明。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以作品将南北各家、东西各方集于一堂。86位作家,有鲁迅、茅盾、郑振铎等前辈大家,又有巴金、沈从文、鲁彦、张天翼等当红名家,还有艾芜、曹禺、丽尼、卞之琳等初露头角的作家,尚有刘白羽、陈荒煤等当时名不见经传的文学青年。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不在一个社团,但一生追求光明与进步。
形成一支包罗各方的文艺劲军,这是鲁迅先生生前所希望的。巴金通过文化生活出版社,实现了鲁迅先生的夙愿。
《死魂灵》、《上尉的女儿》、《猎人日记》、《贵族之家》、《凯旋门》、《劳动》、《双城记》、《柔米欧与朱丽叶》、《包法利夫人》、《复活》、《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父与子》、《简爱》、《大卫·高柏菲尔》、《决斗》、《悬崖》、《杜勃洛夫斯基》……一部部世界文学名著,也正是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介绍到中国来的。
随着作品,果戈理、狄更斯、普希金、托尔斯泰、左拉、莫泊桑、福楼拜、屠格涅夫、高尔基、萧伯纳、莎士比亚、司汤达、王尔德、杰克·伦敦、赫尔岑等世界作家,走进中国读者心中。
东西方文化在上海汇流,后浪推前浪,汹涌澎湃。
巴金与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作用,正在被人们认识。陈荒煤在《冬去春来》一文中说道:“从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由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团结作家的面很广,也有不少共产党员和左翼作家的作品。这套丛刊实际展示三十年代开始了一个创作繁荣的新时代,这是现代文学史异常光辉的一页,是任何人也无法抹杀的。”在复旦中文系简陋的办公室,巴金评论家陈思和对记者说:“从某种意义上看,巴金主持的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价值比他本人再写几部书更重要。”
巴金自己又如何看待这段时间的工作?1982年,巴金在《上海文艺出版社三十年》一文中写道:“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了14年,写稿、看稿、编辑、校对,甚至补书,不是为了报酬,是因为人活着需要多做工作,需要发散、消耗自己的精力。我一生始终保持着这样一个信念: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与,而不是在于接受,也不是在于争取。所以做补书的工作我也感到乐趣,能够拿几本新出的书送给朋友,献给读者,我认为是莫大的快乐。”
他还说道:“我过去搞出版工作,编丛书,就依靠两种人:作者和读者。得罪了作家我拿不到稿子;读者不买我编的书,我就无法编下去……因此我常常开玩笑说:‘作家和读者都是我的衣食父母。’我口里这么说的,心里也这么想,工作的时候我一直记住这两种人。”
巴金的故事四:一个从不揩公家油的厚道人
1954年,徐钤由部队转业来到上海文联,在对外友协,负责作家、音乐家的联络工作。今天,徐钤两鬓染白,早已离休。然而,每星期他总有几天,从远离市中心的莘庄,坐上地铁和公交车,花去一个多小时的时辰,来到医院,探望巴金先生,顺便为巴金处理一些事情。
这一生,徐钤接触过许许多多文化名人,惟有对巴金的感情最深。他是在一些细小事情上感受巴金的。一个从不揩公家油的厚道人,这是徐钤对巴金的深刻印象之一。
二楼,巴金书房,北墙处有一尊褐色巴金铜像。这是50年代中期苏联雕塑家谢里汉诺夫雕铸的。徐钤清楚地记得这一幕幕。那会儿,谢里汉诺夫同时为上海好几位文化名人塑像。按中苏两国的协议,谢里汉诺夫在沪的吃、住等费用,由上海方面一次付清。因此,他在为文化人塑像期间的用餐,由自己解决。
那一天,轮到巴金了。从小见到拍照就躲,不喜欢出头露面的巴金,“乖乖”地当了回“模特”。在巴金的不自在中,时间流过去了,到了中午时分。谢里汉诺夫在收拾着工具,巴金问道:“中午是休息,还是继续做?”谢说:“都可以。由你定。”巴金关切地问道:“你中午干什么?”谢里汉诺夫答道:“我带了面包,吃一点就可以了。”巴金听后,十分不安,说道:“我也要吃饭,我请你,一起去吃吧。”这样,巴金的塑像雕了3天,巴金请谢里汉诺夫吃了3天的饭。
徐钤说:“巴金就是这样一个厚道的人,总想着别人。”
那会儿,在外事方面,一般送外宾的礼品,都是由公家买的。甚至,一些头儿或名人,在家里接待客人,连茶水、点心,都是由公家买好后送了去的。只有巴金从不这样,所有接待外宾的费用,都是掏自己的腰包。通常,礼品都由夫人萧珊买,会面结束时,拿出来送客人。
巴金的这一“习惯”,保持到今天,反映在方方面面。1960年,巴金回到故乡成都,四川歌舞团正在上演《刘三姐》。一天,巴金请沙汀代买8张票,请大家看戏。有关方面知道了,决定送票给巴金。巴金坚决不要,说道:“我请人看戏,必须自己花钱。”80年代,巴金有过几次出国机会。每次回来后,都是由巴金出钱,请大家吃一顿后再“散伙”。那次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日,同行的有冰心、艾芜、杜鹏程等人。回国后,在上海作总结。按理,会后应该由中国作协请大家吃饭。但是,没有。还是由巴金出钱,在静安宾馆订了二桌,请大家吃了一顿,尔后各奔东西。
徐钤说:“巴老就是这么一个人,从不揩公家的油。所以,我敬佩他,愿意终身为他服务。”
巴金的故事五:你是巴金的儿子?
1993年,巴金90岁生日时,上海市政协主席陈铁迪来访。走进巴金寓所,陈铁迪看到自己属下的工作人员李小棠,便有点奇怪地说了一句:“你怎么也来了?”这时,有人赶紧告诉她:小棠是巴金的儿子。
“你是巴金的儿子?我怎么不知道?”陈铁迪惊异地问起来。
陈铁迪当然不知道。在小棠身上,一点也看不到名人之后的影子。他自己也从来不在别人面前提起父亲。在这个家里,凡需要“出头露面”的事,小棠一概推到了姐姐小林的身上,他总是躲在幕后。巴金年迈后,出访时需要家人陪伴左右,方便照料,这时也都是姐姐出面,他不参与。总之,在以巴金为主的公众活动中,难以看到小棠的身影。以至于,有人玩笑地说:“见小棠比见巴金都难。”
小棠在复旦大学读书4年,学校许多领导都不知道他是巴金的儿子。毕业分配时,很多人为子女能分到一个好单位,这里托人,那儿找人,千方百计搞关系,走后门。惟有巴金,没有跟任何人打过招呼。小棠的很多同学,这个留在了学校,那个到了中央大单位,这个进了报社,那个去了电视台……通俗点说,在那时,很多人分配的工作都比小棠好。而小棠来到上海市政协文史室工作,这一干就是20多年,没有一点怨言。
在儿子的身上,可以看到巴金的许多影子。和父亲一样,小棠外表沉稳,不善言谈,不喜张扬,但不乏幽默。有一年,巴金在杭州休息,小棠去看父亲,钱包不慎在火车上被人扒了。到了巴金住所,小棠说了钱包被偷的事,完了,把手一摊,对巴金说:“老巴金,赔我钱。”巴金可不“糊涂”,说道:“你的钱被人偷了,为啥子要我赔。”“我是来看你,才被人偷的。我没有钱,要你赔。”小棠“强词夺理”。巴金“回敬”道:“你多写几部电视剧,钱就有了。”看着他们父子“唇枪舌剑”,一旁的工作人员都乐了。
参考资料:http://www.huaxia.com/zt/2003-58/whbl/00149983.html
汽车库、储藏室、阁楼上、楼道口、阳台前、厕所间、客厅里、卧房内……在巴金偌大的寓所内,曾经到处是书。巴金爱书,在文化圈内是出了名的。他的藏书之多,在当代文人中,恐怕无人可比。
藏书多,自然在于书买得多。
巴金胞弟李济生曾谈起四哥爱书、买书的情况:“说到他最喜爱的东西,还是书。这一兴趣从小到老没有变。在法国过着穷学生的清苦生活时,省吃俭用余下来的钱,就是买自己喜爱的书。有了稿费收入,个人生活不愁,自然更要买书。‘1·28’日本侵略军的炮火毁去了他的住处,收藏的书也随之毁了。习惯已成,兴趣所在,书慢慢地又积累起来。去日本小住1年,就买了许多英日文版书带回来。有的名家作品他会不遗余力地搜集各种文字的译本。住屋几乎全放满了书。解放后搬了家,房子宽敞了,书架、书橱也随之增多增大。书房内四壁皆书,客厅内也顺墙壁一溜立上4只大书橱,连走廊上、过道上也放有书橱。一句话,无处不是书了。”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巴金一家生活已很拮据,只剩下57元银元。萧珊从菜场买来价廉的小黄鱼和青菜,用盐腌起来,晾干。每天取出一点,就算全家有了荤腥蔬菜吃了。这两只菜,竟然支撑了全家半年的伙食。
一天傍晚,楼梯传来巴金沉重的脚步。萧珊和养子绍弥迎了上去,只见他提着两大包刚买的书,气喘喘的。萧珊问道:“又买书了?”“嗯,当然要买书了。”巴金回答道。从来就十分尊重,也什么都依着巴金的萧珊,这时说了一句:“家里已经没有什么钱了。”巴金问也不问家里到底还有多少钱,日子能不能过下去,就说道:“钱,就是用来买书的。都不买书,写书人怎么活法?”
第2天,他又带着孩子们去逛书店了。
巴金买书真的没商量。
在现存的300多封巴金与萧珊的通信中,有不少内容是关于寄钱买书的。1949年9月20日巴金书信萧珊:“昨天刚寄出一信,今早又收到你的信了。我还没有到开明去拿钱,过两天我会去拿的。其实我自己也不需要多少钱,不过来北平一趟总得买点东西带回去送人,我自己也想买几本书。”从中可以看出,巴金这时在北京,准备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巴金已寄信嘱萧珊汇钱来,等不及又发信回去。
这是一封巴金写于1956年6月23日的信,其中有这样一段:“这次买书较少,已寄了几包回去,大概还有几包。”已寄了几包回去,还有几包,这还是买得少的,那么多的呢?可以想像,巴金买书有多“狠”。这次寄信的地点也是在北京。据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巴金去北京,没有一次不买书回来的。琉璃厂、王府井,都是巴金必去的地方。
巴金的故事二:称自己的作品百分之五十是废品
《巴金全集》26卷,700来万字。这是巴金献给人类的一笔巨大财富。
文人多自尊,多轻狂,多自以为是。世上少有赞叹别人的文人,更鲜有批评自己的文人。所谓“文人相轻”,不仅有道理,而且是一个普遍现象。
巴金却说自己“不”。这个“不”,不是他在《随想录》中对自己灵魂的拷问,而是对自己的文学成就,文学生命:他说,他的作品,百分之五十是废品。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人民文学出版社拟出版《巴金全集》。起初,巴金不同意。编辑王仰晨几次来沪做说服工作,被王仰晨的热情和决心打动,一年后巴金终于同意了。
巴金为何不同意出版他的《全集》?巴金说,编印《全集》是对自己的一次惩罚。因为,他认为,他的作品百分之五十不合格,是废品。
巴金是无情的。他说,第4卷中的《死去的太阳》,是一篇幼稚之作,第5卷中的《利娜》,严格地说还不是“创作”。他认为《砂丁》和《雪》都是失败之作。这两篇小说,写于30年代初,以矿工生活为题材。他虽然在长兴煤矿住过一个星期,但是对矿工的生活,了解的还只是皮毛。因此,编造的成分很大。尽管如此,当时统治者很害怕这两篇小说,发行不久就遭到查禁。《雪》的原名叫《萌芽》,重印时改为《雪》。
巴金是严厉的。在读者中广为流传的《爱情三部曲》,他也说是不成功之作。在《巴金全集》第6卷“代跋”中,巴金开篇就写道:“《爱情三部曲》也不是成功之作。关于这三卷书我讲过不少夸张的话,甚至有些装腔作势。我说我喜欢它们,1936年我写《总序》的时候,我的感情是真诚的。今天我重读小说中某些篇章,我的心仍然不平静,不过我不像从前那样的喜欢它们了,我看到了一些编造的东西。有人批评我写革命‘上无领导、下无群众’,说这样的革命是空想,永远‘革’不起来。说得对!我没有一点革命的经验。也可以说,我没有写革命的‘本钱’。我只是想为一些熟人画像,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使我感动的发光的东西。我拿着画笔感到毫无办法时,就求助于想象,求助于编造,企图给人物增添光彩,结果却毫无所得。”
巴金是苛刻的。他还说《火》是失败之作。《火》也是三部曲。说它是失败之作,巴金多次讲过。在编选《巴金选集》时,也没有把它们收进去。巴金说:“我不掩盖自己的缺点。但写一个短篇,不一定会暴露我的缺点。写中篇、长篇那就不同了,离不了生活,少不了对生活的感受。生活不够,感受不深,只好避实就虚,因此写出了肤浅的作品。”关于《火》,巴金还说:“三卷《火》中我写了两位熟人……但是我应该承认跟我这样熟的两个人我都没有写好……除了刚才说的‘避实就虚’外,我还有一个毛病,我做文章一贯信笔写去,不是想好才写。我没有计划,没有蓝图,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所以我不是艺术家,也不是文学家,更不是什么大师。我只是用笔做武器,靠作品生活,在作品中进行战斗。我经常战败,倒下去,又爬起来,继续战斗。”
巴金是彻底的。他觉得,他在一些文章中写了自己不想说的话,写了自己不理解的事情。在一些作品里,他还写了许多不切实际的豪言壮语,与读者的距离越来越远。他的百分之五十废品的观点,自然不被人们认同。编辑王仰晨首先在给巴金的信中表达了异议。巴金回信道:“说到废品你不同意,你以为我谦虚。你不同意我那百分之五十的废品的看法。但是,重读过去的文章,我绝不能宽恕自己。有人责问我为什么把自己搞得这样痛苦,正因为我无法使笔下的豪言壮举成为现实。”
巴金是理智的。他清晰地看到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化。所以,他说:“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青年把我当作他们的朋友……在十八九岁的日子,热情像一锅煮沸的油,谁也愿意贡献出自己宝贵的血。我写了一本又一本的书,一次又一次地送到年轻读者手中。我感觉到我们之间的友谊在加深。但是二十年后,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青年就不理解我了。我感到寂寞、孤独,因为我老了,我的书也老了,无论怎样修饰、加工,也不能给它们增加多少生命。你不用替我惋惜,不是他们离开我,是我离开了他们。我的时代可能已经过去。我理解了自己,就不会感动遗憾,也希望读者理解我。”
一个睿智的人,一个真诚的人,一个可敬的人——巴金。
巴金的故事三:出书献给读者是莫大的快乐
中国文学和中国出版史上,留有值得大书的一页: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这个由吴朗西、巴金等人创办的小小的同仁出版社,却为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从1935年创办到1954年公私合营,出版社出版发行了28种丛刊、专集、选集,计有226部作品。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书,是经总编辑巴金的手编排发印的。
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当年的老编辑、巴金胞弟李济生整理的图书出版目录中,我们看到了一长串在中国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作品:《故事新编》、《骆驼祥子》、《边陲线上》、《憩园》、《第三代》、《淘金记》、《前夕》、《八骏图》、《路》、《团圆》、《南行记》、《运河》、《饭余集》、《雷雨》、《日出》……长篇、中篇、短篇、散文、诗歌、戏剧……涵盖各个文学门类。
鲁迅、茅盾、老舍、巴金、沈从文、曹禺、汪曾祺、李健吾、靳以、艾芜、沙汀、郑振铎、黄源、穆旦、何其芳、唐弢、萧乾、李广田、师陀、黄棠、王西彦、黎烈文、柯灵、鲁彦、方令儒、芦焚、张天翼、王统照、肖军、胡风、罗洪、吴组缃、丽尼、欧阳山、陈荒煤、刘白羽、艾青、卞之琳、臧克家、端木蕻良、陈白尘、曹葆华、冯至……86位作家, 在中国文学史上,灿若星际。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文坛流派纷呈,社团众多,阵营分明。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以作品将南北各家、东西各方集于一堂。86位作家,有鲁迅、茅盾、郑振铎等前辈大家,又有巴金、沈从文、鲁彦、张天翼等当红名家,还有艾芜、曹禺、丽尼、卞之琳等初露头角的作家,尚有刘白羽、陈荒煤等当时名不见经传的文学青年。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不在一个社团,但一生追求光明与进步。
形成一支包罗各方的文艺劲军,这是鲁迅先生生前所希望的。巴金通过文化生活出版社,实现了鲁迅先生的夙愿。
《死魂灵》、《上尉的女儿》、《猎人日记》、《贵族之家》、《凯旋门》、《劳动》、《双城记》、《柔米欧与朱丽叶》、《包法利夫人》、《复活》、《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父与子》、《简爱》、《大卫·高柏菲尔》、《决斗》、《悬崖》、《杜勃洛夫斯基》……一部部世界文学名著,也正是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介绍到中国来的。
随着作品,果戈理、狄更斯、普希金、托尔斯泰、左拉、莫泊桑、福楼拜、屠格涅夫、高尔基、萧伯纳、莎士比亚、司汤达、王尔德、杰克·伦敦、赫尔岑等世界作家,走进中国读者心中。
东西方文化在上海汇流,后浪推前浪,汹涌澎湃。
巴金与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作用,正在被人们认识。陈荒煤在《冬去春来》一文中说道:“从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由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团结作家的面很广,也有不少共产党员和左翼作家的作品。这套丛刊实际展示三十年代开始了一个创作繁荣的新时代,这是现代文学史异常光辉的一页,是任何人也无法抹杀的。”在复旦中文系简陋的办公室,巴金评论家陈思和对记者说:“从某种意义上看,巴金主持的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价值比他本人再写几部书更重要。”
巴金自己又如何看待这段时间的工作?1982年,巴金在《上海文艺出版社三十年》一文中写道:“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了14年,写稿、看稿、编辑、校对,甚至补书,不是为了报酬,是因为人活着需要多做工作,需要发散、消耗自己的精力。我一生始终保持着这样一个信念: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与,而不是在于接受,也不是在于争取。所以做补书的工作我也感到乐趣,能够拿几本新出的书送给朋友,献给读者,我认为是莫大的快乐。”
他还说道:“我过去搞出版工作,编丛书,就依靠两种人:作者和读者。得罪了作家我拿不到稿子;读者不买我编的书,我就无法编下去……因此我常常开玩笑说:‘作家和读者都是我的衣食父母。’我口里这么说的,心里也这么想,工作的时候我一直记住这两种人。”
巴金的故事四:一个从不揩公家油的厚道人
1954年,徐钤由部队转业来到上海文联,在对外友协,负责作家、音乐家的联络工作。今天,徐钤两鬓染白,早已离休。然而,每星期他总有几天,从远离市中心的莘庄,坐上地铁和公交车,花去一个多小时的时辰,来到医院,探望巴金先生,顺便为巴金处理一些事情。
这一生,徐钤接触过许许多多文化名人,惟有对巴金的感情最深。他是在一些细小事情上感受巴金的。一个从不揩公家油的厚道人,这是徐钤对巴金的深刻印象之一。
二楼,巴金书房,北墙处有一尊褐色巴金铜像。这是50年代中期苏联雕塑家谢里汉诺夫雕铸的。徐钤清楚地记得这一幕幕。那会儿,谢里汉诺夫同时为上海好几位文化名人塑像。按中苏两国的协议,谢里汉诺夫在沪的吃、住等费用,由上海方面一次付清。因此,他在为文化人塑像期间的用餐,由自己解决。
那一天,轮到巴金了。从小见到拍照就躲,不喜欢出头露面的巴金,“乖乖”地当了回“模特”。在巴金的不自在中,时间流过去了,到了中午时分。谢里汉诺夫在收拾着工具,巴金问道:“中午是休息,还是继续做?”谢说:“都可以。由你定。”巴金关切地问道:“你中午干什么?”谢里汉诺夫答道:“我带了面包,吃一点就可以了。”巴金听后,十分不安,说道:“我也要吃饭,我请你,一起去吃吧。”这样,巴金的塑像雕了3天,巴金请谢里汉诺夫吃了3天的饭。
徐钤说:“巴金就是这样一个厚道的人,总想着别人。”
那会儿,在外事方面,一般送外宾的礼品,都是由公家买的。甚至,一些头儿或名人,在家里接待客人,连茶水、点心,都是由公家买好后送了去的。只有巴金从不这样,所有接待外宾的费用,都是掏自己的腰包。通常,礼品都由夫人萧珊买,会面结束时,拿出来送客人。
巴金的这一“习惯”,保持到今天,反映在方方面面。1960年,巴金回到故乡成都,四川歌舞团正在上演《刘三姐》。一天,巴金请沙汀代买8张票,请大家看戏。有关方面知道了,决定送票给巴金。巴金坚决不要,说道:“我请人看戏,必须自己花钱。”80年代,巴金有过几次出国机会。每次回来后,都是由巴金出钱,请大家吃一顿后再“散伙”。那次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日,同行的有冰心、艾芜、杜鹏程等人。回国后,在上海作总结。按理,会后应该由中国作协请大家吃饭。但是,没有。还是由巴金出钱,在静安宾馆订了二桌,请大家吃了一顿,尔后各奔东西。
徐钤说:“巴老就是这么一个人,从不揩公家的油。所以,我敬佩他,愿意终身为他服务。”
巴金的故事五:你是巴金的儿子?
1993年,巴金90岁生日时,上海市政协主席陈铁迪来访。走进巴金寓所,陈铁迪看到自己属下的工作人员李小棠,便有点奇怪地说了一句:“你怎么也来了?”这时,有人赶紧告诉她:小棠是巴金的儿子。
“你是巴金的儿子?我怎么不知道?”陈铁迪惊异地问起来。
陈铁迪当然不知道。在小棠身上,一点也看不到名人之后的影子。他自己也从来不在别人面前提起父亲。在这个家里,凡需要“出头露面”的事,小棠一概推到了姐姐小林的身上,他总是躲在幕后。巴金年迈后,出访时需要家人陪伴左右,方便照料,这时也都是姐姐出面,他不参与。总之,在以巴金为主的公众活动中,难以看到小棠的身影。以至于,有人玩笑地说:“见小棠比见巴金都难。”
小棠在复旦大学读书4年,学校许多领导都不知道他是巴金的儿子。毕业分配时,很多人为子女能分到一个好单位,这里托人,那儿找人,千方百计搞关系,走后门。惟有巴金,没有跟任何人打过招呼。小棠的很多同学,这个留在了学校,那个到了中央大单位,这个进了报社,那个去了电视台……通俗点说,在那时,很多人分配的工作都比小棠好。而小棠来到上海市政协文史室工作,这一干就是20多年,没有一点怨言。
在儿子的身上,可以看到巴金的许多影子。和父亲一样,小棠外表沉稳,不善言谈,不喜张扬,但不乏幽默。有一年,巴金在杭州休息,小棠去看父亲,钱包不慎在火车上被人扒了。到了巴金住所,小棠说了钱包被偷的事,完了,把手一摊,对巴金说:“老巴金,赔我钱。”巴金可不“糊涂”,说道:“你的钱被人偷了,为啥子要我赔。”“我是来看你,才被人偷的。我没有钱,要你赔。”小棠“强词夺理”。巴金“回敬”道:“你多写几部电视剧,钱就有了。”看着他们父子“唇枪舌剑”,一旁的工作人员都乐了。
参考资料:http://www.huaxia.com/zt/2003-58/whbl/00149983.html
第2个回答 推荐于2018-01-26
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爱情的三部曲》(《雾》、《雨》、《电》),《憩园》,散文集《随想录》 。
巴金的故事一:钱,是用来买书的
巴金胞弟李济生曾谈起四哥爱书、买书的情况:“说到他最喜爱的东西,还是书。这一兴趣从小到老没有变。在法国过着穷学生的清苦生活时,省吃俭用余下来的钱,就是买自己喜爱的书。有了稿费收入,个人生活不愁,自然更要买书。‘1·28’日本侵略军的炮火毁去了他的住处,收藏的书也随之毁了。习惯已成,兴趣所在,书慢慢地又积累起来。去日本小住1年,就买了许多英日文版书带回来。有的名家作品他会不遗余力地搜集各种文字的译本。住屋几乎全放满了书。解放后搬了家,房子宽敞了,书架、书橱也随之增多增大。书房内四壁皆书,客厅内也顺墙壁一溜立上4只大书橱,连走廊上、过道上也放有书橱。一句话,无处不是书了。”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巴金一家生活已很拮据,只剩下57元银元。萧珊从菜场买来价廉的小黄鱼和青菜,用盐腌起来,晾干。每天取出一点,就算全家有了荤腥蔬菜吃了。这两只菜,竟然支撑了全家半年的伙食。
一天傍晚,楼梯传来巴金沉重的脚步。萧珊和养子绍弥迎了上去,只见他提着两大包刚买的书,气喘喘的。萧珊问道:“又买书了?”“嗯,当然要买书了。”巴金回答道。从来就十分尊重,也什么都依着巴金的萧珊,这时说了一句:“家里已经没有什么钱了。”巴金问也不问家里到底还有多少钱,日子能不能过下去,就说道:“钱,就是用来买书的。都不买书,写书人怎么活法?”
第2天,他又带着孩子们去逛书店了。
巴金买书真的没商量。
在现存的300多封巴金与萧珊的通信中,有不少内容是关于寄钱买书的。1949年9月20日巴金书信萧珊:“昨天刚寄出一信,今早又收到你的信了。我还没有到开明去拿钱,过两天我会去拿的。其实我自己也不需要多少钱,不过来北平一趟总得买点东西带回去送人,我自己也想买几本书。”从中可以看出,巴金这时在北京,准备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巴金已寄信嘱萧珊汇钱来,等不及又发信回去。
巴金的故事二:称自己的作品百分之五十是废品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人民文学出版社拟出版《巴金全集》。起初,巴金不同意。编辑王仰晨几次来沪做说服工作,被王仰晨的热情和决心打动,一年后巴金终于同意了。
巴金为何不同意出版他的《全集》?巴金说,编印《全集》是对自己的一次惩罚。因为,他认为,他的作品百分之五十不合格,是废品。
巴金的故事三:出书献给读者是莫大的快乐
中国文学和中国出版史上,留有值得大书的一页: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这个由吴朗西、巴金等人创办的小小的同仁出版社,却为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从1935年创办到1954年公私合营,出版社出版发行了28种丛刊、专集、选集,计有226部作品。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书,是经总编辑巴金的手编排发印的。
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当年的老编辑、巴金胞弟李济生整理的图书出版目录中,我们看到了一长串在中国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作品:《故事新编》、《骆驼祥子》、《边陲线上》、《憩园》、《第三代》、《淘金记》、《前夕》、《八骏图》、《路》、《团圆》、《南行记》、《运河》、《饭余集》、《雷雨》、《日出》……长篇、中篇、短篇、散文、诗歌、戏剧……涵盖各个文学门类。
鲁迅、茅盾、老舍、巴金、沈从文、曹禺、汪曾祺、李健吾、靳以、艾芜、沙汀、郑振铎、黄源、穆旦、何其芳、唐弢、萧乾、李广田、师陀、黄棠、王西彦、黎烈文、柯灵、鲁彦、方令儒、芦焚、张天翼、王统照、肖军、胡风、罗洪、吴组缃、丽尼、欧阳山、陈荒煤、刘白羽、艾青、卞之琳、臧克家、端木蕻良、陈白尘、曹葆华、冯至……86位作家, 在中国文学史上,灿若星际。
巴金的故事四:一个从不揩公家油的厚道人
1954年,徐钤由部队转业来到上海文联,在对外友协,负责作家、音乐家的联络工作。今天,徐钤两鬓染白,早已离休。然而,每星期他总有几天,从远离市中心的莘庄,坐上地铁和公交车,花去一个多小时的时辰,来到医院,探望巴金先生,顺便为巴金处理一些事情。
这一生,徐钤接触过许许多多文化名人,惟有对巴金的感情最深。他是在一些细小事情上感受巴金的。一个从不揩公家油的厚道人,这是徐钤对巴金的深刻印象之一。
二楼,巴金书房,北墙处有一尊褐色巴金铜像。这是50年代中期苏联雕塑家谢里汉诺夫雕铸的。徐钤清楚地记得这一幕幕。那会儿,谢里汉诺夫同时为上海好几位文化名人塑像。按中苏两国的协议,谢里汉诺夫在沪的吃、住等费用,由上海方面一次付清。因此,他在为文化人塑像期间的用餐,由自己解决。
那一天,轮到巴金了。从小见到拍照就躲,不喜欢出头露面的巴金,“乖乖”地当了回“模特”。在巴金的不自在中,时间流过去了,到了中午时分。谢里汉诺夫在收拾着工具,巴金问道:“中午是休息,还是继续做?”谢说:“都可以。由你定。”巴金关切地问道:“你中午干什么?”谢里汉诺夫答道:“我带了面包,吃一点就可以了。”巴金听后,十分不安,说道:“我也要吃饭,我请你,一起去吃吧。”这样,巴金的塑像雕了3天,巴金请谢里汉诺夫吃了3天的饭。
徐钤说:“巴金就是这样一个厚道的人,总想着别人。”
那会儿,在外事方面,一般送外宾的礼品,都是由公家买的。甚至,一些头儿或名人,在家里接待客人,连茶水、点心,都是由公家买好后送了去的。只有巴金从不这样,所有接待外宾的费用,都是掏自己的腰包。通常,礼品都由夫人萧珊买,会面结束时,拿出来送客人。
巴金的故事五:你是巴金的儿子?
1993年,巴金90岁生日时,上海市政协主席陈铁迪来访。走进巴金寓所,陈铁迪看到自己属下的工作人员李小棠,便有点奇怪地说了一句:“你怎么也来了?”这时,有人赶紧告诉她:小棠是巴金的儿子。
“你是巴金的儿子?我怎么不知道?”陈铁迪惊异地问起来。本回答被提问者和网友采纳
巴金的故事一:钱,是用来买书的
巴金胞弟李济生曾谈起四哥爱书、买书的情况:“说到他最喜爱的东西,还是书。这一兴趣从小到老没有变。在法国过着穷学生的清苦生活时,省吃俭用余下来的钱,就是买自己喜爱的书。有了稿费收入,个人生活不愁,自然更要买书。‘1·28’日本侵略军的炮火毁去了他的住处,收藏的书也随之毁了。习惯已成,兴趣所在,书慢慢地又积累起来。去日本小住1年,就买了许多英日文版书带回来。有的名家作品他会不遗余力地搜集各种文字的译本。住屋几乎全放满了书。解放后搬了家,房子宽敞了,书架、书橱也随之增多增大。书房内四壁皆书,客厅内也顺墙壁一溜立上4只大书橱,连走廊上、过道上也放有书橱。一句话,无处不是书了。”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巴金一家生活已很拮据,只剩下57元银元。萧珊从菜场买来价廉的小黄鱼和青菜,用盐腌起来,晾干。每天取出一点,就算全家有了荤腥蔬菜吃了。这两只菜,竟然支撑了全家半年的伙食。
一天傍晚,楼梯传来巴金沉重的脚步。萧珊和养子绍弥迎了上去,只见他提着两大包刚买的书,气喘喘的。萧珊问道:“又买书了?”“嗯,当然要买书了。”巴金回答道。从来就十分尊重,也什么都依着巴金的萧珊,这时说了一句:“家里已经没有什么钱了。”巴金问也不问家里到底还有多少钱,日子能不能过下去,就说道:“钱,就是用来买书的。都不买书,写书人怎么活法?”
第2天,他又带着孩子们去逛书店了。
巴金买书真的没商量。
在现存的300多封巴金与萧珊的通信中,有不少内容是关于寄钱买书的。1949年9月20日巴金书信萧珊:“昨天刚寄出一信,今早又收到你的信了。我还没有到开明去拿钱,过两天我会去拿的。其实我自己也不需要多少钱,不过来北平一趟总得买点东西带回去送人,我自己也想买几本书。”从中可以看出,巴金这时在北京,准备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巴金已寄信嘱萧珊汇钱来,等不及又发信回去。
巴金的故事二:称自己的作品百分之五十是废品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人民文学出版社拟出版《巴金全集》。起初,巴金不同意。编辑王仰晨几次来沪做说服工作,被王仰晨的热情和决心打动,一年后巴金终于同意了。
巴金为何不同意出版他的《全集》?巴金说,编印《全集》是对自己的一次惩罚。因为,他认为,他的作品百分之五十不合格,是废品。
巴金的故事三:出书献给读者是莫大的快乐
中国文学和中国出版史上,留有值得大书的一页: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这个由吴朗西、巴金等人创办的小小的同仁出版社,却为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从1935年创办到1954年公私合营,出版社出版发行了28种丛刊、专集、选集,计有226部作品。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书,是经总编辑巴金的手编排发印的。
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当年的老编辑、巴金胞弟李济生整理的图书出版目录中,我们看到了一长串在中国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作品:《故事新编》、《骆驼祥子》、《边陲线上》、《憩园》、《第三代》、《淘金记》、《前夕》、《八骏图》、《路》、《团圆》、《南行记》、《运河》、《饭余集》、《雷雨》、《日出》……长篇、中篇、短篇、散文、诗歌、戏剧……涵盖各个文学门类。
鲁迅、茅盾、老舍、巴金、沈从文、曹禺、汪曾祺、李健吾、靳以、艾芜、沙汀、郑振铎、黄源、穆旦、何其芳、唐弢、萧乾、李广田、师陀、黄棠、王西彦、黎烈文、柯灵、鲁彦、方令儒、芦焚、张天翼、王统照、肖军、胡风、罗洪、吴组缃、丽尼、欧阳山、陈荒煤、刘白羽、艾青、卞之琳、臧克家、端木蕻良、陈白尘、曹葆华、冯至……86位作家, 在中国文学史上,灿若星际。
巴金的故事四:一个从不揩公家油的厚道人
1954年,徐钤由部队转业来到上海文联,在对外友协,负责作家、音乐家的联络工作。今天,徐钤两鬓染白,早已离休。然而,每星期他总有几天,从远离市中心的莘庄,坐上地铁和公交车,花去一个多小时的时辰,来到医院,探望巴金先生,顺便为巴金处理一些事情。
这一生,徐钤接触过许许多多文化名人,惟有对巴金的感情最深。他是在一些细小事情上感受巴金的。一个从不揩公家油的厚道人,这是徐钤对巴金的深刻印象之一。
二楼,巴金书房,北墙处有一尊褐色巴金铜像。这是50年代中期苏联雕塑家谢里汉诺夫雕铸的。徐钤清楚地记得这一幕幕。那会儿,谢里汉诺夫同时为上海好几位文化名人塑像。按中苏两国的协议,谢里汉诺夫在沪的吃、住等费用,由上海方面一次付清。因此,他在为文化人塑像期间的用餐,由自己解决。
那一天,轮到巴金了。从小见到拍照就躲,不喜欢出头露面的巴金,“乖乖”地当了回“模特”。在巴金的不自在中,时间流过去了,到了中午时分。谢里汉诺夫在收拾着工具,巴金问道:“中午是休息,还是继续做?”谢说:“都可以。由你定。”巴金关切地问道:“你中午干什么?”谢里汉诺夫答道:“我带了面包,吃一点就可以了。”巴金听后,十分不安,说道:“我也要吃饭,我请你,一起去吃吧。”这样,巴金的塑像雕了3天,巴金请谢里汉诺夫吃了3天的饭。
徐钤说:“巴金就是这样一个厚道的人,总想着别人。”
那会儿,在外事方面,一般送外宾的礼品,都是由公家买的。甚至,一些头儿或名人,在家里接待客人,连茶水、点心,都是由公家买好后送了去的。只有巴金从不这样,所有接待外宾的费用,都是掏自己的腰包。通常,礼品都由夫人萧珊买,会面结束时,拿出来送客人。
巴金的故事五:你是巴金的儿子?
1993年,巴金90岁生日时,上海市政协主席陈铁迪来访。走进巴金寓所,陈铁迪看到自己属下的工作人员李小棠,便有点奇怪地说了一句:“你怎么也来了?”这时,有人赶紧告诉她:小棠是巴金的儿子。
“你是巴金的儿子?我怎么不知道?”陈铁迪惊异地问起来。本回答被提问者和网友采纳
相似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