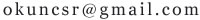哲学一开始便不是科学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这本身是历史的一个基本事实。可也是由于历史的某些原因,今天,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哲学依然被自觉不自觉地当做“科学”来对待。你肯定听到过或者亲口说过,“这种世界观是不科学的”,“你这哲学观点是伪科学”,“某某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等等。
科学是评价哲学的标准?哲学的本质是科学?或者说,哲学是科学中的一种?在历史中,为了说明它们的不同,那些透顶聪明的大脑也算开足马力绞尽脑汗地拿主意想办法:有人给我们打比方说,知识好比是大树,哲学是树根,科学则是树枝(笛卡尔);有人说,哲学和科学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哲学是普遍性,科学是特殊性(斯大林);更早有人说,哲学是人类天性中喜欢寻根问底的好奇倾向,是超越经验的“在物理学之后的”“第一哲学”(亚里士多德);有学生给黑格尔写信抱怨哲学太艰涩、太“抽象”(我们今天的许多学生依然与那些早已作古的老学生非常想象),黑格尔回信说,只有科学才是抽象的,而哲学却恰好是具体的;而今甚至有一派干脆认为,哲学与科学在本质上没有任何联系,哲学只是思维的一种逻辑或能力;等等。
在历史上,也有过把哲学当做科学来对待的时期,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之前的自然哲学时期。当时,哲学试图包容所有的具体科学,且不自量力地充任“科学的科学”,结果被马克思等后起之秀“革”了它们的“命”。马克思一方面肯定了科学在历史变革中的作为推进力量的作用,另方面又指出只有哲学才是批判现实世界的“思想武器”。恩格斯甚至非常哲学地接过黑格尔的那句屡遭误解的名言“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经过辩证的推演,得出的结论刚好是,凡是现存的,最终都要归于灭亡。于此,哲学并不是科学,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在阶级斗争中,在社会实践中起着科学所不能替代的“武器”作用。正因为此,马克思干脆称自己的哲学为“实践的”唯物论。
完全把哲学等同于科学的做法,是包括自然哲学家们在内的任何人所不能同意的。但不自觉地把哲学当作一种科学的却大有人在。如果寻找历史的原因,人们将会发现,近代科学的迅猛发展在大力改变着自然和社会的同时,理性主义思潮和情绪也日趋膨胀,就像商品社会里人们向往的金钱,科学似乎成了战无不胜的法宝,成了人类精神依恋慕拜的对象。对科学的崇拜式的、迷信式的或者“相信”式的教育,造成了人们价值观念系统的变形。于是,精神领域里的一切都变成了科学的附庸。正因为此,人们再一次逃脱不了那条古老的定律:物极必反!于此,科学开始走向了它竭尽全力所反对的对立面:迷信。可见,理清哲学和科学的关系,不仅是关系到哲学的生存空间问题,也是关系到科学自身的发展问题。
人类什么时候有了哲学?为什么要思考什么“哲学”?这大概是哲学发生论的第一个问题。经验着的人们有了经验和科学作为自己的生存工具真的不够用?这个问题是十分玄妙的,以至于在整个东西方哲学和科学史上,那些充满睿智的脑袋们也没有给出一个人们共同认可的标准答案。朱熹曾回忆说,他在四五岁的时候就开始琢磨“天外”有什么“物事”,——经验着的人们对这样望天发痴的小孩肯定是疑惑不解,可这或计又是这位后来的“圣人”的第一次“哲学”思考。——朱熹为什么要去“琢磨”?康德说,哲学是人类理性要求的结果。可是,“理性”究竟有哪些要求?科学不够吗?亚里士多德说,哲学诞生在有闲暇的地方,——这倒真有点吃饱了没事干的意思——又说,是人们与生俱来的好奇心的结果。这些理论几乎都是抽象人性论的合理延伸,其实本质问题并没有得到回答。这好像在说,你为什么要吃饭,答:因为饿了!
哲学在历史上的出现,肯定是出于特定的需要。或许,它出现的原因与宗教、原始艺术诞生原因是完全一样的;或许,它们正是同一个母腹里的孪生兄弟。可什么是那“特定的需要”呢?三言两语是无法解释它的;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这种“需要”与需要科学诞生的“需要”是不同的。人们可以合乎逻辑地追问,原始人为什么要在岩洞里留下他们的壁画?这个问题非常类似与朱熹为什么会在四五岁的时候要去思考天外有什么物事的问题。岩洞里的壁画决不会帮助原始人获得更多的粮食和猎物。他们愿意花那么多的工夫(“工夫”一词非常耐人寻味,它不完全指谓“时间”,更多的意味是指“劳动”,无疑,壁画的创作是一种劳动,而并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享受“闲暇”)去做一件看来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实惠的事情,是出于什么动机?唯一能解释的是,类似于壁画创作的活动能获得不同于衣食住行之类的满足或享受。
而科学诞生的原因是人类生存的需要。对农作物的最早试种肯定是农业科学的第一次试验,然后,他们在经验中,逐步发现农作物的丰产与气候、土壤、品种等等有密切关系。农业科学如此,别的科学门类也不例外,几乎所有的科学都是以满足人类的衣食住行为依归的。从本质上看,科学是人类经验的合乎逻辑的自然延伸。至于今天的专门的“科研人员”,那自然是社会分工的结果。它围绕我们的生活需要劳神费力。由此来看,神秘而神圣的科学殿堂其实是在做一件普通的事情。
从心理距离上说,较之于科学,哲学、宗教、艺术似乎离我们更远。这也是我们觉得更需要科学的原因。科学在与人们的直接需要打交道,它在满足人类直接需要的同时,又把这种需要推至新的阶段。于是,我们愈来愈需要和依赖科学。而觉得哲学完全是可有可无的,好像哲学只是人们精神的奢侈品。自然,这是近视的看法,或者说是一叶障目。因为,人之为人,并不完全等同于其他的动物。人类的精神需要是其他的动物们所没有的。原始人在与自然抗争的同时,便发出了真正意义上的“天问”。或者惊奇于自己完美无缺的体态,或者惊喜于自然按部就班的秩序,或者惊恐于鬼神莫测的风雨雷电,这些都可能触发他们的灵感,唤起他们的天赋智性和联想,来“读世界这本大书”。于是,对自然“本质”的领悟,诞生了那最高的“天人合一”的妙论。
当然,在人类知识的萌芽时期,一切都处于含苞待放的浑沌状态,知识几乎没有门类的区别,也没有后来意义上的哲学和科学的明确的界限。就像母腹中的婴儿,对于现实的人而言,他(她)还只是一种可能性,最多也只是正在走向现实“人”的可能性。但是,就像婴儿已包涵着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几乎全部的信息,哲学和科学的后来“分家,此时已被决定。后来的发展只是形态上的展开,而其发展的方向,逻辑并不是自由地漫步,而已先在地受到限制。一棵树无论长得多大多高,多么的气势恢宏,其实不过是那颗小种子的外在展开而已。由于哲学与科学满足的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的不同方面,所以,它们的差异已经先在地本质地存在着。
从发生论的角度看,哲学和科学的产生都是多方面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环境的因素,也有人类在适应环境过程中建构起来的智力、天性、心理的因素。其中人自身的多维的需要尽管不是最后的决定因素,——辩证唯物论认为,“需要”本身也是受决定的——但它的确起着无可置疑的直接推动作用。在我们熟悉的经验生活中,往往是直接的需要遮挡了间接的需要,意识层面的需要模糊了非理性层面的需要;换句话说,很多时候,人们只能或只要知道自己的部分或少部分的需要。而就人类的智力能力来说,被经验意识覆盖着的领悟、直觉等等那种扬弃片面奔整体的能力,常常只出现在极端境遇的非经验的那一刹那。犹如岩洞壁画的创作者精神从树皮兽骨山洞中突然解放出来的灵感;犹如那净饭王子菩提树下的顿悟;犹如泰勒斯从生命的源头发现了水;犹如曹臣相醉后的歌唱;……有人说,艺术是本能的升华,在此意义上无疑是贴切的。其实除了艺术,哲学、宗教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它们之不同于科学首先在于,它们是以人类之先在的集体无意识张扬更广阔的需要,升华深层的非理性本能。
如果说,科学的宗旨在于解决或者方便人类的生活,那么,哲学却致于透视人类的生存;科学旨在认识,哲学功在觉悟。
何为哲学?真正贴切的解答是没有的。从中文里的“哲”所指谓的意思看,类似于觉悟、智慧、这与西文中的“爱智慧”的说法非常一致。而“科学”最初的意思应该是实用的知识。在“试错”活动(“实验”活动的机制)中诞生了科学,而哲学却是智慧的结果,也可以说,是思想“解放”的结果,是深层意念的觉醒的结果。
由于产生的起点不同,哲学和科学在本质是根本不同的。
“本质”的不同的首要原因是两者所指向的对象的不同。科学有两个意义上的对象:一是各相对独立的科学门类各有属于自己的研究领域。也正因为此,科学才有了门类的区别,有了被叫做“物理”“生物”“信息”的学问。其二,科学的对象还可以被理解为“事实”。“事实”的特征是特定的、有形的、相对稳定的。也就是说,可以被“认定”的。无法“认定”的东西不能称为科学意义上的“事实”。科学的任务在于探究事实及其事实间的“关系”,诸如必然关系、或然关系、先后关系、因果关系,等等。从这两层意义上看,科学的对象是特定的,具体的,所以科学才又被叫做“具体科学”。可是,这里的具体正好与辩证法意义上的“具体”意思相反!辩证法的“具体”指的是片面的综合或抽象的综合,是对科学的那种“具体”的超越和扬弃。正因为此,黑格尔才把科学称为“抽象的”而哲学才是“具体的”。换句话说,科学的“抽象”就是因为它的对象的特定或“具体”!我们这些“具体”的人因此会觉得我们是多么的需要科学,而那虚无缥缈的玄而又玄的哲学似乎跟我们的生活挨不上边。
“玄”,应当是哲学的初始而又贴切的说法。玄,说出了哲学对象的基本特征。“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差不多说出了科学和哲学对象上的区别。哲学并不指向“具体的”事实或事情。“理在事先”(朱熹的高论),这被当作唯心主义批判了好些年,放在这里却十分合适。科学在论“事”,哲学却在论“理”。较之于“事”或“器”,“理”当然是先在的,或者说,更为“本质的”。哲学最初正是作为追问世界的“原理”而出现的,至今,仍然以此为出发点。“原理”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再灵敏的鼻子也是嗅不出来的,高倍的显微镜也是找不出来的,所以,它超出了人们的感性“具体”;给这样的东西寻找合适的词,非“玄”莫属!可是,“玄”有什么好处呢?换句话说,哲学有什么用处呢?古人似乎专门为此作了注释:因为玄,所以妙!因为玄是“众妙之门”。今天,我们常常使用“玄妙”一词,却经常丢了它的意思。哲学本是最容不得实用主义的,可今天它居然玄妙到有了“实用主义”哲学!“实用”不是“适用”,哲学看起来不能教会我们具体的“本领”,比如说,不能直接的帮助我们去赚钱,所以它很不实用!但是,所有的“本领”(或曰“众妙”)包括科学,无论如何的高妙,最终又离不开哲学,所以,它又是“适用”的。
马克思曾借用黑格尔的话表达过“玄”:“非对象性”。“非对象性”是对哲学的对象的特征的一种描述,说明哲学的对象既有也无——由此看来,魏晋玄学的“有”“无”之争实乃事有出因——所谓“有”,任何的“学问”必定有其起因、缘由及“对象”,否则,何以许多的学说被同时冠以“哲学”之头衔?所谓“无”,哲学又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学问”,它的确没有通常意义的“对象”。好比说,你觉得心烦,可你又找不出心烦的具体原由。哲学也是如此。我们既不能说哲学是研究某一具体对象,又不能说它不是一种“研究”。因此,准确的说法只能是,哲学的对象是超乎具体对象的。有没有“超乎”具体对象的东西?是有的。比如说,你见过许多“美”的事物,可你并不知道什么是“美”本身,你做了许多“善”举,可你能解释什么是“善”?生活中我们会碰到许多“圆”的东西,但它们似乎都不够圆,最圆的那个“圆”在哪里?善、美、圆、诸如此类,在指谓什么?它或它们有没有“具体的”好象?没有!更有甚者,康德说,人类的理解程度是有限的,当我们对“片面”进行综合时,荒谬、背反必定出现。依照“科学的”康德哲学只能是荒谬的化身。在此意义上,康德也像“许多的有学问”的人,骨子里依然是理性慕拜的科学家。因为,“荒谬”一词,本无特定的涵义,其本质是对经验的背叛。哲学对象的“非对象性”,对经验和科学而言,无疑是一种荒谬。这种“荒谬”用中文来说,就是“玄”。
玄,代表着有限相对的无限,代表着变化中的不变,代表着片面之后的全面,代表着相对性扬弃后的绝对,一句话,哲学指向的是人们深层受其影响和制约而几乎又全然不知的经验之外的“世界”。用科学的语言来说,这是一个“可能的”“理念的”“非常的”“心理的”世界。尽管如此,可又不能说它是一个“虚幻的”“捏造的”世界。玄之为妙,奥妙就在这里!就像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骨子里一定会怕点什么,我们生活的“真实”往往是一种更富有欺骗性的虚幻。“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代表了虚幻破灭后的觉悟。佛教哲学以极大的耐心给人们展示了一个超越了我们眼睛的“空”的世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有山有水非常“实”在的世界,可佛眼看去,眼中的那些个事物都是有条件而存在的(因“缘”而生灭),而条件的存在又是要条件的,依此类推,无条件而“独立”存在的具体事物是没有的,因此,唯一的真实是“空”或“无”。“空”也很玄,没有了我们赖以生存的万事万物,心里的确玄的着慌。可是,当我们一旦了解了万物的条件性、暂时性、过渡性,我们是不是能更为自主自觉的生存呢?我们是不是从此能抛开虚幻的懦弱的懵懂的生存方式,继而转向一种紧定而有序的新的生命航程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哲学,在对象上与宗教、艺术是一致的。它们指向的都是超乎“现在”世界——所谓的“现存”其实是人类经验和科学所观照出来的——的“可能”世界。这里的“可能”并不是不真实,而是更高意义上的真实。犹如空气看不见摸不着,所以人们长期以来一直称之为“空”,可我们须臾也离不开它。无疑,“可能”的世界是通过人们的心理反思所建构起来的,所以,它又是一个理念的世界。我们发现在生活中任何美的事物都是有缺陷的,何来的“发现”?这就是心里的一次以自身深层理念为坐标的、不自觉的反思活动。换句话说,既然“现存”中并没有那最美的样板,那么,最美的那个“美”只能在人们的“理念”中。理念中的那个“美”,只是一种“可能”,但是,在特定的意义上,它是更高的真实。
无疑,人类生存的“世界”只有一个。问题的关键是,在不同的主体面前,呈现出来的却是不同的世界。科学和哲学“看”到的世界是截然不同的!哲学历史中出现的“双重”、“多重”世界的理论的确体现了主体的自我觉醒。佛教哲学给人们展示了三重世界:是——非——非非。这里,并不是说有三个世界,而是说,在三种主体面前,世界会显现出三种“样子”。盲人摸象的故事的确意味深长。科学无疑面对的是“是”“非”的世界,因而,其本质在求“真”,于是有了真假、是非、对错的区别和对立。而哲学等却引导人们走进“非非”之境,因而有了庄子之类的“逍遥游”,在那里,是非、大小、真假等等——在经验的眼睛里,它们之间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鸿沟——失去了对立的意义。无疑,这是一个与科学世界大相径庭的“玄妙”的世界。
黑格尔曾经断言,哲学与宗教、艺术在对象上相通,而在形式上相别;哲学与科学在方法上相通,而对象上不同。确实,黑格尔除了他个人的高瞻远瞩的哲学天才以外,他更主要的仍是那个时代的理性主义的代言人。那里,科学在经验生活中产生的效果令人迷醉,对科学的依恋之情成为时代的特征,一些科学著作成为新娘出嫁的必备嫁妆。尽管黑格尔也曾讥笑过农业杂志刊登哲学文章这种科学哲学不分的作法,但他本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以哲学来包容科学的自然哲学家。尽管科学与哲学在历史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是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大有其人,但是,这决不意味着黑格尔的科学哲学方法相同的论点就能成立。
方法,当是服务于特定目的的手段或方式,同样的目的可以有不同的方法,相同的目的也可以有相同的方法。科学与哲学在方法上的确有相同之处,但是,由于根本目的不同,方法上也存在着本质的差异。
科学的方法在本质上是经验方法或这种方法的延伸和变化。它以观察、实验(重复经验)、证实为前提,在本质上,它是默默的以客体为中心,绕着客体转,观察到的东西(表象)被“整理”压缩为某种“关系”、“定理”、“规律”或“本质”,在这里,“本质”仅仅是众多现象的一种简便的称呼。休谟说得好,习惯是人生的伟大指南!——中国也有句类似的话,习惯成自然,自然,本是本质性的意思,这说明了“习惯”的力量是何等的巨大——休谟在对我们说,经验重复的次数多了,就“变”成了“事实”,你看到太阳从东边出来,且天天如此,于是你会对太阳明天仍从东边升起毫不怀疑,巴浦洛夫对狗做的实验也说明了“习惯”的作用。中国还有一句话,实践出真知。其意是说,不断地去做,你就会有效地学到其中的“学问”。实际上,这种“学问”依然是由多次的经验的重复而“总结”出来的,换句话说,是习惯让我们得到“证实”。
科学的方法本质上正是这样一种以客体为中心、以经验证明或证实为基础、不断重复验证为手段而寻找“本质”或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的经验方法。这种方法更有效地帮助人们“看清”经验世界,让人们能更“方便”地生活。简言之,这是一种经验证实的方法——波普尔“证伪”理论的提出不仅没有改变它的本质,而是从另一方面让人们看清它的本质。因为,“证伪”依然是为了证“实”,证伪不过是证实的运行机制罢了!
可是,什么是“证实”?换言之,什么是“事实”?我们的科学曾认定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是事实,后来认为太阳是中心是事实,后来又认为太阳只是银河系里的一颗普通的星星,这是不是“最终”的事实呢?应当说,科学史上的所有理论几乎都得到过证实,今天我们依然可以说,如果宇宙本是无限的,那么,什么都可以是“中心”;如果以地球为坐标,怎么又不能说太阳是绕着地球转呢?什么才是真正的事实呢?“事实”的一次又一次的被证“伪”一方面构成了科学“发展”的图景,另一方面也在昭示人们,科学和经验本身有着不可避免的盲点或误区!
潜力几乎是无限的智慧让人们觉醒。苏格拉底、柏拉图用极其感性、直观当然也很粗糙的比喻给人们展示了人类经验可悲的景象:人,我们这些人,实际是被禁锢在一间小而黑暗的房子里,我们被迫面对着一堵墙,只是对着我们的后脑勺的墙上有一小窗户,我们永远只能“看”到由那小窗户投射对面墙上的光线和影子,那就是我们常说的“世界”或“外部世界”,人类的全部知识都是在对这个影子的世界进行认识。我们如何能跳出这个井底的世界,如何能摆脱影子的世界而直面真实的世界?柏拉图给了我们一条出路:转向。把脑袋“转”过去!
“转向”,是哲学史上一个十分重要意味深长而又容易遗忘的概念。其实,所谓“哲”的学问或“智慧”的学问本质上正是“转向”的结果,换句话说,“转向”构成了哲学的方法的本质!佛教哲学有一个与此非常一致的说法:“回头”,全部的佛教都是在教人们做“回头”或觉悟的工夫。
转向,是一个动作,可又不是容易做到的动作。好像是躺在床上的植物人要突然清醒过来睁开双眼一样,并不那么轻易地做到。这就是佛学要人们“修炼”的原因。后来的哲学也有一个半新半旧的词:“反思”“直觉”,词是新的,意思是旧的,还是做“转向”的工夫。转向的不易,首要的缘由是我们的“看”世界的视线被死死地捆在经验世界或感性世界上。我们乐于井底的世界,它似乎温暖如春而又安全可靠,它甚至能满足我们的全部需要。因此,几乎没有理由去做那个转向的动作。“智慧是一种痛苦”,算是说到了绝处。在灵魂上做“猛回头”的事情是痛苦的睁开眼睛。哲学里没有天堂或地狱,只在经验的眼睛里,经验之外的世界被看作不是天堂就是地狱;而哲学只在做一件事,反过头来“再看看”我们的经验世界。这里,世界依然是一个,经验和科学生活在(或沉浸在)这一世界中,“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而哲学和智慧却要跳出这个世界再回头来观照它。
转向,或者反思是哲学的基本方法。它不是描述,不是拍照,不是实验,甚至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研究”,——在此意义,尼采曾发宏论,真正的哲学家都是没有读过几本哲学书的!谬哉、妙哉!——因为它在本质上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不是“观察的”,而是觉醒的,不是直接的,而是“反射的”。在现代哲学里,尽管哲学家之间的思想日益疏离,甚至相互漠然不解,但在下面这点上却不谋而合:科学是“思维经济”(马赫语)的产物,哲学却是人类思想直沉觉“解放”的结果,这种解放不是由考察客体引起的,而是主体在主客体的交融中实现的。这是一种“非理性”“非意识”“艺术的”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习惯认定的“真”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就像照片上的那棵树并不是拍摄的那棵树,它只是被摄的那棵树的某一个侧面的“样子”,而那棵树本身却有无数的“侧面”。人们依照经验的方法认定的“客观”其实是相当主观的。因此,哲学的方法必定是对经验和科学状态的超越或省悟,或曰,反思。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的方法又可以说是精神的自我批评自我超越的能力。就像我们可以从一幅天才般的绘画作品里观照出对世界“新”的理解、新的境界,哲学在不断地对我们的经验世界作出评判。而这种“评判”是任何科学仪器或设备做不出来的。
当然,哲学与哲学之间也有一个相互评判的问题。但其完全不同于科学与伪科学之间的对立。前者之间并没有“是非”的对抗,因为哲学本来就不是关于是非的学问。而后者的对立却是是非之争。确实,是非的对立只是在非常有限的意义上才是有效的,要不怎么说,“真理往前走一步可能就是谬误”。哲学间的对立实际是看世界方法的对立。
科学是评价哲学的标准?哲学的本质是科学?或者说,哲学是科学中的一种?在历史中,为了说明它们的不同,那些透顶聪明的大脑也算开足马力绞尽脑汗地拿主意想办法:有人给我们打比方说,知识好比是大树,哲学是树根,科学则是树枝(笛卡尔);有人说,哲学和科学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哲学是普遍性,科学是特殊性(斯大林);更早有人说,哲学是人类天性中喜欢寻根问底的好奇倾向,是超越经验的“在物理学之后的”“第一哲学”(亚里士多德);有学生给黑格尔写信抱怨哲学太艰涩、太“抽象”(我们今天的许多学生依然与那些早已作古的老学生非常想象),黑格尔回信说,只有科学才是抽象的,而哲学却恰好是具体的;而今甚至有一派干脆认为,哲学与科学在本质上没有任何联系,哲学只是思维的一种逻辑或能力;等等。
在历史上,也有过把哲学当做科学来对待的时期,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之前的自然哲学时期。当时,哲学试图包容所有的具体科学,且不自量力地充任“科学的科学”,结果被马克思等后起之秀“革”了它们的“命”。马克思一方面肯定了科学在历史变革中的作为推进力量的作用,另方面又指出只有哲学才是批判现实世界的“思想武器”。恩格斯甚至非常哲学地接过黑格尔的那句屡遭误解的名言“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经过辩证的推演,得出的结论刚好是,凡是现存的,最终都要归于灭亡。于此,哲学并不是科学,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在阶级斗争中,在社会实践中起着科学所不能替代的“武器”作用。正因为此,马克思干脆称自己的哲学为“实践的”唯物论。
完全把哲学等同于科学的做法,是包括自然哲学家们在内的任何人所不能同意的。但不自觉地把哲学当作一种科学的却大有人在。如果寻找历史的原因,人们将会发现,近代科学的迅猛发展在大力改变着自然和社会的同时,理性主义思潮和情绪也日趋膨胀,就像商品社会里人们向往的金钱,科学似乎成了战无不胜的法宝,成了人类精神依恋慕拜的对象。对科学的崇拜式的、迷信式的或者“相信”式的教育,造成了人们价值观念系统的变形。于是,精神领域里的一切都变成了科学的附庸。正因为此,人们再一次逃脱不了那条古老的定律:物极必反!于此,科学开始走向了它竭尽全力所反对的对立面:迷信。可见,理清哲学和科学的关系,不仅是关系到哲学的生存空间问题,也是关系到科学自身的发展问题。
人类什么时候有了哲学?为什么要思考什么“哲学”?这大概是哲学发生论的第一个问题。经验着的人们有了经验和科学作为自己的生存工具真的不够用?这个问题是十分玄妙的,以至于在整个东西方哲学和科学史上,那些充满睿智的脑袋们也没有给出一个人们共同认可的标准答案。朱熹曾回忆说,他在四五岁的时候就开始琢磨“天外”有什么“物事”,——经验着的人们对这样望天发痴的小孩肯定是疑惑不解,可这或计又是这位后来的“圣人”的第一次“哲学”思考。——朱熹为什么要去“琢磨”?康德说,哲学是人类理性要求的结果。可是,“理性”究竟有哪些要求?科学不够吗?亚里士多德说,哲学诞生在有闲暇的地方,——这倒真有点吃饱了没事干的意思——又说,是人们与生俱来的好奇心的结果。这些理论几乎都是抽象人性论的合理延伸,其实本质问题并没有得到回答。这好像在说,你为什么要吃饭,答:因为饿了!
哲学在历史上的出现,肯定是出于特定的需要。或许,它出现的原因与宗教、原始艺术诞生原因是完全一样的;或许,它们正是同一个母腹里的孪生兄弟。可什么是那“特定的需要”呢?三言两语是无法解释它的;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这种“需要”与需要科学诞生的“需要”是不同的。人们可以合乎逻辑地追问,原始人为什么要在岩洞里留下他们的壁画?这个问题非常类似与朱熹为什么会在四五岁的时候要去思考天外有什么物事的问题。岩洞里的壁画决不会帮助原始人获得更多的粮食和猎物。他们愿意花那么多的工夫(“工夫”一词非常耐人寻味,它不完全指谓“时间”,更多的意味是指“劳动”,无疑,壁画的创作是一种劳动,而并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享受“闲暇”)去做一件看来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实惠的事情,是出于什么动机?唯一能解释的是,类似于壁画创作的活动能获得不同于衣食住行之类的满足或享受。
而科学诞生的原因是人类生存的需要。对农作物的最早试种肯定是农业科学的第一次试验,然后,他们在经验中,逐步发现农作物的丰产与气候、土壤、品种等等有密切关系。农业科学如此,别的科学门类也不例外,几乎所有的科学都是以满足人类的衣食住行为依归的。从本质上看,科学是人类经验的合乎逻辑的自然延伸。至于今天的专门的“科研人员”,那自然是社会分工的结果。它围绕我们的生活需要劳神费力。由此来看,神秘而神圣的科学殿堂其实是在做一件普通的事情。
从心理距离上说,较之于科学,哲学、宗教、艺术似乎离我们更远。这也是我们觉得更需要科学的原因。科学在与人们的直接需要打交道,它在满足人类直接需要的同时,又把这种需要推至新的阶段。于是,我们愈来愈需要和依赖科学。而觉得哲学完全是可有可无的,好像哲学只是人们精神的奢侈品。自然,这是近视的看法,或者说是一叶障目。因为,人之为人,并不完全等同于其他的动物。人类的精神需要是其他的动物们所没有的。原始人在与自然抗争的同时,便发出了真正意义上的“天问”。或者惊奇于自己完美无缺的体态,或者惊喜于自然按部就班的秩序,或者惊恐于鬼神莫测的风雨雷电,这些都可能触发他们的灵感,唤起他们的天赋智性和联想,来“读世界这本大书”。于是,对自然“本质”的领悟,诞生了那最高的“天人合一”的妙论。
当然,在人类知识的萌芽时期,一切都处于含苞待放的浑沌状态,知识几乎没有门类的区别,也没有后来意义上的哲学和科学的明确的界限。就像母腹中的婴儿,对于现实的人而言,他(她)还只是一种可能性,最多也只是正在走向现实“人”的可能性。但是,就像婴儿已包涵着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几乎全部的信息,哲学和科学的后来“分家,此时已被决定。后来的发展只是形态上的展开,而其发展的方向,逻辑并不是自由地漫步,而已先在地受到限制。一棵树无论长得多大多高,多么的气势恢宏,其实不过是那颗小种子的外在展开而已。由于哲学与科学满足的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的不同方面,所以,它们的差异已经先在地本质地存在着。
从发生论的角度看,哲学和科学的产生都是多方面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环境的因素,也有人类在适应环境过程中建构起来的智力、天性、心理的因素。其中人自身的多维的需要尽管不是最后的决定因素,——辩证唯物论认为,“需要”本身也是受决定的——但它的确起着无可置疑的直接推动作用。在我们熟悉的经验生活中,往往是直接的需要遮挡了间接的需要,意识层面的需要模糊了非理性层面的需要;换句话说,很多时候,人们只能或只要知道自己的部分或少部分的需要。而就人类的智力能力来说,被经验意识覆盖着的领悟、直觉等等那种扬弃片面奔整体的能力,常常只出现在极端境遇的非经验的那一刹那。犹如岩洞壁画的创作者精神从树皮兽骨山洞中突然解放出来的灵感;犹如那净饭王子菩提树下的顿悟;犹如泰勒斯从生命的源头发现了水;犹如曹臣相醉后的歌唱;……有人说,艺术是本能的升华,在此意义上无疑是贴切的。其实除了艺术,哲学、宗教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它们之不同于科学首先在于,它们是以人类之先在的集体无意识张扬更广阔的需要,升华深层的非理性本能。
如果说,科学的宗旨在于解决或者方便人类的生活,那么,哲学却致于透视人类的生存;科学旨在认识,哲学功在觉悟。
何为哲学?真正贴切的解答是没有的。从中文里的“哲”所指谓的意思看,类似于觉悟、智慧、这与西文中的“爱智慧”的说法非常一致。而“科学”最初的意思应该是实用的知识。在“试错”活动(“实验”活动的机制)中诞生了科学,而哲学却是智慧的结果,也可以说,是思想“解放”的结果,是深层意念的觉醒的结果。
由于产生的起点不同,哲学和科学在本质是根本不同的。
“本质”的不同的首要原因是两者所指向的对象的不同。科学有两个意义上的对象:一是各相对独立的科学门类各有属于自己的研究领域。也正因为此,科学才有了门类的区别,有了被叫做“物理”“生物”“信息”的学问。其二,科学的对象还可以被理解为“事实”。“事实”的特征是特定的、有形的、相对稳定的。也就是说,可以被“认定”的。无法“认定”的东西不能称为科学意义上的“事实”。科学的任务在于探究事实及其事实间的“关系”,诸如必然关系、或然关系、先后关系、因果关系,等等。从这两层意义上看,科学的对象是特定的,具体的,所以科学才又被叫做“具体科学”。可是,这里的具体正好与辩证法意义上的“具体”意思相反!辩证法的“具体”指的是片面的综合或抽象的综合,是对科学的那种“具体”的超越和扬弃。正因为此,黑格尔才把科学称为“抽象的”而哲学才是“具体的”。换句话说,科学的“抽象”就是因为它的对象的特定或“具体”!我们这些“具体”的人因此会觉得我们是多么的需要科学,而那虚无缥缈的玄而又玄的哲学似乎跟我们的生活挨不上边。
“玄”,应当是哲学的初始而又贴切的说法。玄,说出了哲学对象的基本特征。“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差不多说出了科学和哲学对象上的区别。哲学并不指向“具体的”事实或事情。“理在事先”(朱熹的高论),这被当作唯心主义批判了好些年,放在这里却十分合适。科学在论“事”,哲学却在论“理”。较之于“事”或“器”,“理”当然是先在的,或者说,更为“本质的”。哲学最初正是作为追问世界的“原理”而出现的,至今,仍然以此为出发点。“原理”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再灵敏的鼻子也是嗅不出来的,高倍的显微镜也是找不出来的,所以,它超出了人们的感性“具体”;给这样的东西寻找合适的词,非“玄”莫属!可是,“玄”有什么好处呢?换句话说,哲学有什么用处呢?古人似乎专门为此作了注释:因为玄,所以妙!因为玄是“众妙之门”。今天,我们常常使用“玄妙”一词,却经常丢了它的意思。哲学本是最容不得实用主义的,可今天它居然玄妙到有了“实用主义”哲学!“实用”不是“适用”,哲学看起来不能教会我们具体的“本领”,比如说,不能直接的帮助我们去赚钱,所以它很不实用!但是,所有的“本领”(或曰“众妙”)包括科学,无论如何的高妙,最终又离不开哲学,所以,它又是“适用”的。
马克思曾借用黑格尔的话表达过“玄”:“非对象性”。“非对象性”是对哲学的对象的特征的一种描述,说明哲学的对象既有也无——由此看来,魏晋玄学的“有”“无”之争实乃事有出因——所谓“有”,任何的“学问”必定有其起因、缘由及“对象”,否则,何以许多的学说被同时冠以“哲学”之头衔?所谓“无”,哲学又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学问”,它的确没有通常意义的“对象”。好比说,你觉得心烦,可你又找不出心烦的具体原由。哲学也是如此。我们既不能说哲学是研究某一具体对象,又不能说它不是一种“研究”。因此,准确的说法只能是,哲学的对象是超乎具体对象的。有没有“超乎”具体对象的东西?是有的。比如说,你见过许多“美”的事物,可你并不知道什么是“美”本身,你做了许多“善”举,可你能解释什么是“善”?生活中我们会碰到许多“圆”的东西,但它们似乎都不够圆,最圆的那个“圆”在哪里?善、美、圆、诸如此类,在指谓什么?它或它们有没有“具体的”好象?没有!更有甚者,康德说,人类的理解程度是有限的,当我们对“片面”进行综合时,荒谬、背反必定出现。依照“科学的”康德哲学只能是荒谬的化身。在此意义上,康德也像“许多的有学问”的人,骨子里依然是理性慕拜的科学家。因为,“荒谬”一词,本无特定的涵义,其本质是对经验的背叛。哲学对象的“非对象性”,对经验和科学而言,无疑是一种荒谬。这种“荒谬”用中文来说,就是“玄”。
玄,代表着有限相对的无限,代表着变化中的不变,代表着片面之后的全面,代表着相对性扬弃后的绝对,一句话,哲学指向的是人们深层受其影响和制约而几乎又全然不知的经验之外的“世界”。用科学的语言来说,这是一个“可能的”“理念的”“非常的”“心理的”世界。尽管如此,可又不能说它是一个“虚幻的”“捏造的”世界。玄之为妙,奥妙就在这里!就像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骨子里一定会怕点什么,我们生活的“真实”往往是一种更富有欺骗性的虚幻。“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代表了虚幻破灭后的觉悟。佛教哲学以极大的耐心给人们展示了一个超越了我们眼睛的“空”的世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有山有水非常“实”在的世界,可佛眼看去,眼中的那些个事物都是有条件而存在的(因“缘”而生灭),而条件的存在又是要条件的,依此类推,无条件而“独立”存在的具体事物是没有的,因此,唯一的真实是“空”或“无”。“空”也很玄,没有了我们赖以生存的万事万物,心里的确玄的着慌。可是,当我们一旦了解了万物的条件性、暂时性、过渡性,我们是不是能更为自主自觉的生存呢?我们是不是从此能抛开虚幻的懦弱的懵懂的生存方式,继而转向一种紧定而有序的新的生命航程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哲学,在对象上与宗教、艺术是一致的。它们指向的都是超乎“现在”世界——所谓的“现存”其实是人类经验和科学所观照出来的——的“可能”世界。这里的“可能”并不是不真实,而是更高意义上的真实。犹如空气看不见摸不着,所以人们长期以来一直称之为“空”,可我们须臾也离不开它。无疑,“可能”的世界是通过人们的心理反思所建构起来的,所以,它又是一个理念的世界。我们发现在生活中任何美的事物都是有缺陷的,何来的“发现”?这就是心里的一次以自身深层理念为坐标的、不自觉的反思活动。换句话说,既然“现存”中并没有那最美的样板,那么,最美的那个“美”只能在人们的“理念”中。理念中的那个“美”,只是一种“可能”,但是,在特定的意义上,它是更高的真实。
无疑,人类生存的“世界”只有一个。问题的关键是,在不同的主体面前,呈现出来的却是不同的世界。科学和哲学“看”到的世界是截然不同的!哲学历史中出现的“双重”、“多重”世界的理论的确体现了主体的自我觉醒。佛教哲学给人们展示了三重世界:是——非——非非。这里,并不是说有三个世界,而是说,在三种主体面前,世界会显现出三种“样子”。盲人摸象的故事的确意味深长。科学无疑面对的是“是”“非”的世界,因而,其本质在求“真”,于是有了真假、是非、对错的区别和对立。而哲学等却引导人们走进“非非”之境,因而有了庄子之类的“逍遥游”,在那里,是非、大小、真假等等——在经验的眼睛里,它们之间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鸿沟——失去了对立的意义。无疑,这是一个与科学世界大相径庭的“玄妙”的世界。
黑格尔曾经断言,哲学与宗教、艺术在对象上相通,而在形式上相别;哲学与科学在方法上相通,而对象上不同。确实,黑格尔除了他个人的高瞻远瞩的哲学天才以外,他更主要的仍是那个时代的理性主义的代言人。那里,科学在经验生活中产生的效果令人迷醉,对科学的依恋之情成为时代的特征,一些科学著作成为新娘出嫁的必备嫁妆。尽管黑格尔也曾讥笑过农业杂志刊登哲学文章这种科学哲学不分的作法,但他本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以哲学来包容科学的自然哲学家。尽管科学与哲学在历史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是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大有其人,但是,这决不意味着黑格尔的科学哲学方法相同的论点就能成立。
方法,当是服务于特定目的的手段或方式,同样的目的可以有不同的方法,相同的目的也可以有相同的方法。科学与哲学在方法上的确有相同之处,但是,由于根本目的不同,方法上也存在着本质的差异。
科学的方法在本质上是经验方法或这种方法的延伸和变化。它以观察、实验(重复经验)、证实为前提,在本质上,它是默默的以客体为中心,绕着客体转,观察到的东西(表象)被“整理”压缩为某种“关系”、“定理”、“规律”或“本质”,在这里,“本质”仅仅是众多现象的一种简便的称呼。休谟说得好,习惯是人生的伟大指南!——中国也有句类似的话,习惯成自然,自然,本是本质性的意思,这说明了“习惯”的力量是何等的巨大——休谟在对我们说,经验重复的次数多了,就“变”成了“事实”,你看到太阳从东边出来,且天天如此,于是你会对太阳明天仍从东边升起毫不怀疑,巴浦洛夫对狗做的实验也说明了“习惯”的作用。中国还有一句话,实践出真知。其意是说,不断地去做,你就会有效地学到其中的“学问”。实际上,这种“学问”依然是由多次的经验的重复而“总结”出来的,换句话说,是习惯让我们得到“证实”。
科学的方法本质上正是这样一种以客体为中心、以经验证明或证实为基础、不断重复验证为手段而寻找“本质”或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的经验方法。这种方法更有效地帮助人们“看清”经验世界,让人们能更“方便”地生活。简言之,这是一种经验证实的方法——波普尔“证伪”理论的提出不仅没有改变它的本质,而是从另一方面让人们看清它的本质。因为,“证伪”依然是为了证“实”,证伪不过是证实的运行机制罢了!
可是,什么是“证实”?换言之,什么是“事实”?我们的科学曾认定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是事实,后来认为太阳是中心是事实,后来又认为太阳只是银河系里的一颗普通的星星,这是不是“最终”的事实呢?应当说,科学史上的所有理论几乎都得到过证实,今天我们依然可以说,如果宇宙本是无限的,那么,什么都可以是“中心”;如果以地球为坐标,怎么又不能说太阳是绕着地球转呢?什么才是真正的事实呢?“事实”的一次又一次的被证“伪”一方面构成了科学“发展”的图景,另一方面也在昭示人们,科学和经验本身有着不可避免的盲点或误区!
潜力几乎是无限的智慧让人们觉醒。苏格拉底、柏拉图用极其感性、直观当然也很粗糙的比喻给人们展示了人类经验可悲的景象:人,我们这些人,实际是被禁锢在一间小而黑暗的房子里,我们被迫面对着一堵墙,只是对着我们的后脑勺的墙上有一小窗户,我们永远只能“看”到由那小窗户投射对面墙上的光线和影子,那就是我们常说的“世界”或“外部世界”,人类的全部知识都是在对这个影子的世界进行认识。我们如何能跳出这个井底的世界,如何能摆脱影子的世界而直面真实的世界?柏拉图给了我们一条出路:转向。把脑袋“转”过去!
“转向”,是哲学史上一个十分重要意味深长而又容易遗忘的概念。其实,所谓“哲”的学问或“智慧”的学问本质上正是“转向”的结果,换句话说,“转向”构成了哲学的方法的本质!佛教哲学有一个与此非常一致的说法:“回头”,全部的佛教都是在教人们做“回头”或觉悟的工夫。
转向,是一个动作,可又不是容易做到的动作。好像是躺在床上的植物人要突然清醒过来睁开双眼一样,并不那么轻易地做到。这就是佛学要人们“修炼”的原因。后来的哲学也有一个半新半旧的词:“反思”“直觉”,词是新的,意思是旧的,还是做“转向”的工夫。转向的不易,首要的缘由是我们的“看”世界的视线被死死地捆在经验世界或感性世界上。我们乐于井底的世界,它似乎温暖如春而又安全可靠,它甚至能满足我们的全部需要。因此,几乎没有理由去做那个转向的动作。“智慧是一种痛苦”,算是说到了绝处。在灵魂上做“猛回头”的事情是痛苦的睁开眼睛。哲学里没有天堂或地狱,只在经验的眼睛里,经验之外的世界被看作不是天堂就是地狱;而哲学只在做一件事,反过头来“再看看”我们的经验世界。这里,世界依然是一个,经验和科学生活在(或沉浸在)这一世界中,“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而哲学和智慧却要跳出这个世界再回头来观照它。
转向,或者反思是哲学的基本方法。它不是描述,不是拍照,不是实验,甚至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研究”,——在此意义,尼采曾发宏论,真正的哲学家都是没有读过几本哲学书的!谬哉、妙哉!——因为它在本质上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不是“观察的”,而是觉醒的,不是直接的,而是“反射的”。在现代哲学里,尽管哲学家之间的思想日益疏离,甚至相互漠然不解,但在下面这点上却不谋而合:科学是“思维经济”(马赫语)的产物,哲学却是人类思想直沉觉“解放”的结果,这种解放不是由考察客体引起的,而是主体在主客体的交融中实现的。这是一种“非理性”“非意识”“艺术的”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习惯认定的“真”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就像照片上的那棵树并不是拍摄的那棵树,它只是被摄的那棵树的某一个侧面的“样子”,而那棵树本身却有无数的“侧面”。人们依照经验的方法认定的“客观”其实是相当主观的。因此,哲学的方法必定是对经验和科学状态的超越或省悟,或曰,反思。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的方法又可以说是精神的自我批评自我超越的能力。就像我们可以从一幅天才般的绘画作品里观照出对世界“新”的理解、新的境界,哲学在不断地对我们的经验世界作出评判。而这种“评判”是任何科学仪器或设备做不出来的。
当然,哲学与哲学之间也有一个相互评判的问题。但其完全不同于科学与伪科学之间的对立。前者之间并没有“是非”的对抗,因为哲学本来就不是关于是非的学问。而后者的对立却是是非之争。确实,是非的对立只是在非常有限的意义上才是有效的,要不怎么说,“真理往前走一步可能就是谬误”。哲学间的对立实际是看世界方法的对立。
温馨提示:内容为网友见解,仅供参考
相似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