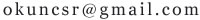自考文学概论的几道测试题目...会的进!
这几道题目找了很久确实没有找到,知道的情帮下忙...尽快啊~~~~多谢! 在亚里斯多德看来,诗人的职责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 ) 古代“境”字一般指疆域边界或乐曲的一段,虚化而用于精神领域首见于( ) “距离论”主张体验是一种拉开功利距离的体会,它的提出者是( ) “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段话是从 的角度来界定文学的。( )
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诗人的职责不在于像历史学家那样描述已经发生过的事,不在于描写历史的真实;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可能发生的事”,这些事是可信的、是带有普遍性的。显然,亚里士多德在艺术(诗)中不是在谋求历史的真实再现,而是在谋求艺术的真实。这种艺术真实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不是在艺术世界中对历史事实的简单重复,而是能表现出未来可能发生的符合历史逻辑的带有普遍意义的事情。 补充: 境——竟,一般指疆域边界或乐曲的一段,虚化用于精神领域始见于 《庄子》 ,《庄子》:“荣辱之境”(《逍遥游》)、“是非之境”(《秋水》)、“振于无境故寓诸无境”(《齐物论》)等。 补充: 西方 美学 上的“距离”论,就是主张体验是一种拉开 功利 距离的体会。“距离”论的提出者 瑞士 心理学家 布洛 (Edward Bullough,1880~1934)提出了一个“雾 海航 行”的例子来说明,他说在大海航行中突然遇到 大雾 ,这对大多数旅客来说,都是极不愉快的经验,伴随着人们的是焦虑、恐惧和紧张等等。但是只要我们把眼前的可能发生的危险等抛在一边,换一种客观的眼光来看这景象,周围的大雾迷迷原原,变成了半透明的乳状的帷幕,这不是很美吗?这里实际上是对已有的经验换了一个角度重新审视,即所谓在 观照 中“插入了距离”。布洛解释说: 距离的作用不是简单的而是相当复杂的。它有否定的抑制的一面——割断事物的实用的方面以及我们对待事物的实践态度,它还有积极的一面——精心制作在距离的抑制作用所创造的新的基础上的经验。因此,这种对事物作有距离的观看,不是也不可能是我们正常的观看。通常,经验总是把同一方面向着我们,即具有最强的时间的 感染力 的方面。一般情况下我们意识不到事物不直接不实际地触及到我们的那些方面,我们一般也意识不到同我们的自己的 接纳 印象的自我相分离的印象。事物颠倒过来,意外地观看通常未注意到的方面,这使我们得到一种启示,这就是 艺术 的启示。 所谓“艺术的启示”也就是在换了一个视角之后,重新审视自己的体验,以便看到通常本注意的方面,即事物的深义和诗意的方面。 补充: 《 论语 ·阳货》载 孔子 语:“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孔子《诗》学思想的高度概括。从内核的层面,它论述了《诗》与 伦理 观念,尤其是“仁”、“礼”的关系;从功能的层面,它表述了《诗》的经世之用与进德之功;从阐释的层面,它点明了《诗》的阐释路径,因为有“可以”,就有一个“如何可以”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就是阐释。下面我们就结合《诗论》,来讨论《诗》是如何“兴”、“观”、“群”、“怨”的,必要时也将应用传世文献中的孔子论《诗》材料。 “兴”,作为阐释学意义的“兴”其实就是“取譬”,而功能意义上的“感发志意”则是“取譬”于《诗》的结果,所以孔安国与 朱熹 的注无所谓谁对谁错,着眼点不同而已。从阐释的形态来看,古人的论说引《诗》基本上是取譬似的,古人引诗每每于结尾处缀以“此之谓也”之习语,译成现代语言就是“××诗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实际上就点出了引《诗》作为譬性思维的取义特征。此外,“赋诗 断章 ”从赋诗者当下的情境看也是取譬似的。所以,以《诗》取譬是先秦人最主要的用《诗》形式。先秦人取譬用《诗》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显性的,就是直接就诗句的字面义来取譬,比如《 论语·述而 》孔子引《小雅·小旻》之“不敢暴虎,不敢 冯河 ,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来批评子路只有血气之勇,却缺乏“临事而惧,好谋而成”的智谋及谨慎。另一种模式是隐性的,也就是从字面不能直接申发出说诗者的含义,需要说诗者“引譬连类”予以发掘,最终突破语言的浅表视域,落到言语之外。就像子夏由孔子“绘事后素”申发出“礼后”那样。同样, 子贡 由“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悟出“贫而乐,富而好礼”的道理,同样也受到孔子的称赞。 无论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取譬,都要 遵从 “类”的约束。在先秦时,“类”是一个 社会学 概念,然后被引进了 语言学 领域。“类”具有 宗法 性和同一性。一旦形之于思维,成为取譬的标准,“类”就有了伦理的和 逻辑 的双重特性。逻辑的标准可以利于思维间关系的构建,以保证取譬的成功。而且“类同”是“有以同”,这就使得取譬的范围可以很广,同一事理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取譬,同一事物也可以用于不同情况下的取譬。如果说事物间的同一性是取譬的外在规定的话,则伦理性的标准就构成了取譬的内在 张力 ,从根本上规范了取譬的方向。子贡、子夏之所以受到孔子的称赞,就是因为他们的取譬是以宗法伦理、修身养德为归依的。有违于此就是“不类”,就像 《左传》 昭公元年,楚令尹歌 《大明》 之首章,俨然以王自取譬,赵孟就讥其“不类”;三家以《雍》彻,孔子也讽刺说:“‘相维辟公, 天子 穆穆 。’奚取于三家之堂?”这都属于取譬不类。 就传世文献来看,孔子论《诗》多为引诗,是“取譬”似的。《诗论》中也有这种取譬解诗形式,第6、7、21、22等简皆是。比如孔子说:“《鸤鸠》吾信之”。《鸤鸠》属 《曹风》 ,《毛诗》以为是刺诗,而孔子则无所谓美刺,他只是取譬于“其仪一兮,心如结”,以说明君子当有均一之德。说“吾信之”不是别的,信“德”也。 “观”, 郑玄 注:“观风俗之盛衰”。朱熹注:“考见得失”,均是 从政 治角度切入的。但我认为如果将“观”作此理解,就与“群”、“怨”,至少与“怨”相包容了,这无疑会削减“兴观群怨”作为理论整体的表述广度。所以“观”至少有两用,施用政治,即为观人情之 厚薄 ,识风俗之盛衰;施用于个人,即为观人“ 情志 ”。而且主体是观人“情志”,因为即便是政治的兴衰也是通过个体的情志反映出来的。从传世文献及上博简《诗论》看,“观”是孔子非常重要的一种解《诗》模式,那种“吾于……见……”、“吾于……知……”、“吾以……得……”等句式就是“观”的视角所特有的 表达方式 。其次,从“观”的角度解《诗》,使得孔子特别重视对 诗歌 中个体情感的把握,形成了以“情志”解《诗》的独特视角。《诗论》解诗,有好几处谈到“志”。比如,第8简其论《小旻》云:“《小旻》多疑矣,言不中志也。”第19简“溺志,既曰天也,犹有怨言”,也当为解某诗语,第26简论《蓼莪》:“《蓼莪》有孝志”,等等。如果说“志”偏向于理性,具有一定的伦理内涵,则“情”就是 心理结构 中的“欲望”,是人本性的真实反映。《诗论》有好几处谈到了“情”,如第9简:“《黄鸟》则困而欲反其故也”,第10简其说《 燕燕 》:“《燕燕》之情”,第18简其说《杕杜》:“《杕杜》则情喜其至也”,第19简说《 木瓜 》:“《木瓜》其藏愿而未得 达也 ”,第25简说《兔爰》:“《有兔》不逢时”,等等。而政治的兴衰,民风的厚薄就寓于诗歌主人公的情感中。比如《诗论》说《兔爰》“不逢时”,何谓“不逢时”?《 说苑 ·敬慎篇》记孔子读《诗》至《正月》之六章,则感慨说:“不逢时之君子,岂不殆哉?从上依世则废道;违上离俗则危身;世不与善,己独由之,则曰非妖则孽也。是以桀杀 关龙 逢,纣杀王子 比干 。故贤者不遇时,常恐不终焉。”所以孔子常说“天下无道则隐”,那么《诗论》以“不逢时”评《兔爰》不就是含有“天下无道”的意思吗?最后,“观”有各种各样的角度,以“观”解诗也就了多重视角。比如《 柏舟 》, 《孔丛子》 说“于《柏舟》见匹夫执志之不可易也”,而《诗论》评《柏舟》曰“闷”。“匹夫执志之不可移”有称赞的意味,而“闷”就有了讥讽意,何哉?因为君子 遁世 无闷,就像《孔丛子》论《考槃》那样。所以《柏舟》的主人公就只能当“匹夫”之谓。 总之,从理论的角度来看用“观”的方法,从“情志”的角度解《诗》,使得孔子对诗旨能有准确的把握,而且是多视角的。这是孔子重“情”的《诗》学思想在解诗中的反映,它使得孔子不仅比此前的解《诗》 高明 ,也比他以后的解《诗》者高明。 “群”,孔安国注:“群居相切磋”。朱熹注:“和而不流”。我认为均不确,“群”就是“别群”,也就是“君子”、“小人”之辨。辨别君子、小人关乎进德, 《论语》 一书,“君子”一词凡107见,“小人”凡23见,每每相较而言,可见孔子对“君子”、“小人”之辨的重视程度。就 《诗经》 而言,有许多诗篇言及“君子”之德,或“小人”之行,故有“君子之诗”,有“小人之诗”。这就形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解《诗》方法,而且这种方法在先秦时还可能比较流行,如 《孟子·告子下》 载高子论《小雅·小弁》为“小人之诗”。这种解诗方式也见诸《诗论》,如第25简“《肠肠》小人”,第27简“《仲氏》君子”就是。或曰,孔子曰《 诗三百 》“ 思无邪 ”,则于“小人之诗”,何以“无邪”?事实上校诸《诗论》可知,孔子并非对所有诗都是持赞成态度,有的也是批评的,如《柏舟》之“闷”,《墙有茨》之“慎密不知言”,还有第28简以“恶而不闵”评诗皆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朱熹《集注》解释“思无邪”为:“凡《诗》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是有道理的。读“君子之诗”,知何以为君子;读“小人之诗”,知何以规避小人,故曰:“诗可以群”。 “怨”,孔安国、郑玄皆注:“刺上政”。朱熹注:“怨而不怒”。二者都将之归于政治,过于褊狭。《诗》固然可以怨刺上政,但绝不仅限于此。翻开《诗经》,怨词满眼,有悯乱嫉恶之怨,有旷夫思妇之怨;既有忧国忧民之思,也有一已之私情,如统统归结为“怨刺上政”,则殊为无据。《诗论》第8简论《雨无正》、《节南山》曰“皆言上之衰,王公耻之”,怨刺的对象是 周天子 ;论《小弁》、《巧言》曰“皆言流人之害”,第9简论《祈父》曰“《祈父》之责,亦有以也”等,皆为刺当权者,概括起来,这些都可以称为“刺上政”。而第17简“《 扬之水 》其爱妇悡”,“悡”,《 说文 》注“恨”,又曰“怠”。但校之今本《诗经》的三首以《扬之水》名篇的诗都不相吻合,当为逸诗。诗写的是 怨妇 之“恨”,就不能归为“刺上政”。第29简“《涉溱》(即《郑风·褰裳》)其绝”是针对“子不我思,岂无他士”而言的,是“爱而不得”的绝 情诗 ,故曰“绝”。这种“怨”也是怨妇之“怨”,非以“刺上政”也。 孔子从“怨”的角度解《诗》也可以看作是对个体情感的 张扬 ,正如他自己在述自己作 《春秋》 之意时说的那样:“诗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所以,以“怨”解诗,也是孔子重“情”《诗》学思想的阐释实践。 以上我们就《诗论》与孔子《诗》学思想的重诂做了简单的论述。我们认为,《诗论》对我们重新认识孔子的《诗》学思想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仅让我们认识到孔子《诗》学思想中重“情”的一面,而且为我们提供了孔子解《诗》的实例,让我们对孔子《诗》学思想的认识落到了具体的实处。而且正确的评价孔子论《诗》、解《诗》重“情”,对于重新构建中国诗 学理论 史也有重要的意义。传统观念认为,先秦只有“诗言志”,而“诗缘情”要到 西晋 时 陆机 《文赋》 出,才出现。那么既然孔子就有了“诗言情”的观念,那么,“诗言志”还会是先秦惟有的诗学观念吗?“诗缘情”还会是魏晋的新风尚吗?
温馨提示:内容为网友见解,仅供参考
无其他回答
相似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