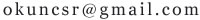[摘 要]张爱玲以其犀利的笔锋揭示在封建社会中被扭曲了的女性,她的《流言》、《传奇》两部作品通过揭示女性心灵充满卑劣、愚昧、丑陋、变态的形象,来表达对封建专制社会的否定,她不依不饶的揭露,以其独特的女性视角探究了封建社会中女性悲剧命运的内因。
[关键词]丑陋;冷漠;独特的视角
[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656(2007)01-0069-04
《流言》、《传奇》是张爱玲的两部作品集,在读者眼前展现了女性特有的形形色色的生命形态。她以女性特有的敏感,去感受都市中女性的生活,描写各式女性的命运,她的笔犹如犀利的解剖刀指向了女性心理,不动声色地向世人揭示了女性心灵充满愚昧、变态的一角,从而呈现出女性孤独、渺小,甚至猥琐、丑陋、无奈的生命原生态。一个女性作家如此诋毁女性,把女人写的如此自私、卑琐、愚昧、变态、贪恋物质,原因何在?有人曾这么说:“看似对男性否定的女性品德进行夸张丑化好似是在狠狠的鞭笞,其实是以退为进,刻意压低女性的声音,以显示男性文化对女性的暴力”。本人认为张爱玲以其独特的女性描写模式,从女性心理、生理两方面揭示出女性在以父权制为中心的文化传统中备受压抑的处境,并从女性深层心理结构上去挖掘其自身的痼疾及其文化根源,凸显女性的人生信念。本文试从张爱玲对女性形象丑陋的的刻画,冷漠的口吻,及独特的视角等几个方面的进行论述。
1丑陋的刻画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对女性形象的刻画落笔在人性深处的阴暗、自私、虚伪、孤独、冷漠。通过张爱玲的作品,我们触摸到了“人性恶”的一面,人的灵魂阴暗与丑陋的一角。张爱玲笔下的人物苍白、渺小,没有高尚的情操,没有善良的心,也没有质朴、憨厚的性格。他们在兽欲、生物性、习俗的挤压下沉沦。中国女性对男性的从属观念经过几千年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残暴的压制,使许多女性自觉地奴化和物化,甚至以此为满足。备受压抑与服从已成为女性的一种生存的习惯。张爱玲毫不留情地拭去所有的粉饰,用冷酷的笔调描述了女性被奴化和钳制的生存状态,她笔下的女性在社会的重压下,心灵被扭曲,性格被异化。
1.1对女性固有“奴性”的否定
自从进入男权社会,中国女性就逐步被规定在小家庭的范围内,恪尽妇人之道,承担着生儿育女、相夫教子之职。由于女性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小,使得她们终日被封闭在与世隔绝的小环境中,个性慢慢散失,这就造成了女性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生活上处处依赖男人,落入了“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的可悲境地。女人想要通过婚姻来抵制生存的威胁,而婚姻在张爱玲笔下是无爱的,“有爱的婚姻是痛苦的”,但婚姻又受不了爱的诱惑。婚姻是枷锁,妄想用它来锁住别人,锁住爱情,都是不可能办到,结果只能毁了自己。腐朽的没落文化封锁住男女间的情爱,美好的情爱被禁锢,被异化,当枷锁打开时,真实的原欲才纷纷现出本来面目,率真自然的感情才得以迸发。
对于未出嫁的女子而言,张爱玲描写的是一部部真真实实的嫁人录。未出嫁的女子都千方百计地要去寻觅一个有钱的男人嫁了,便等于找到了终身寄托,这辈子就有了依靠。《金锁记》里的姜长安遇到从德国归来的章世舫时,才见第一面,便芳心暗许;《倾城之恋》中的离异待嫁的流苏与二十四岁未出阁的宝络、急于找婆家的金枝、金蝉,为吸引范柳原的注意力,更是斗智斗勇,使出浑身解数,目的就是要拴住这个男人的心;《红鸾禧》中的邱玉清以及她的五个装腔作势、卖弄风骚的表妹们,为了吸引男性的注意力更是丑态百出。
对于已成家的女子而言,也不是一帆风顺,高枕无忧的。为了维护自己在家中的地位,为了捍卫自己妻室的身份和头衔,她们忍辱负重、克已待人。《说文解字》中讲道:“妇人,从人者也。”张爱玲写的女性形象无一例外都遵从这条古训。在她笔下的女性虽已走出了旧时代的时光隧道,但她们的心智却还是被困在传统道德和“自我奴化”的囚网中无法自拔。她们为了吸引男性的目光,为了取悦丈夫,竟甘心扮演琐碎、辛苦、卑微、忍让、克己的角色,这就是她们的原生本相,透过这些细节,我们看到的是强悍男性对柔弱女性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人生态度的渗透和支配。
更可悲的是,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大多数是明白自己的处境而自甘堕落,从心理上把自己当作男性的附庸的。恩格斯在谈到被压迫者的生活态度时说过:“只要他们还对统治阶级感到愤怒,他们就仍然是人;但如果他们乖乖地让把挽轭套在脖子上,又想把挽扼下的生活弄得比较过得去一点,而不想摆脱这个挽轭,那他们就真的变成牲口了。”张爱玲笔下的中国老式女儿们在千年传统道德的束缚下,自觉或不自觉地奴化成了“挽轭”下的“牲口”,没有人的自觉,丧失了女性作为人的权利。她们自身甘心为奴的屈服,正配合了外界环境对她们的不公正压迫,使得女性沦为男性附庸地位的接力棒代代相传。
1.2女性形象的物化
在张爱玲小说中注重了人物丑陋的刻画,常给女主人公附上物性。如在《花凋》中郑川嫦在作者眼中是“冷而白的白大蜘蛛”,川嫦则认为自己是没有灯的灯塔;《半生缘》中顾曼璐是“红粉骷髅”;《茉莉香片》中冯碧落是“屏风白鸟”;《金锁记》中七巧是“蝴蝶标本”;《小艾》中小艾也像一只淡漠具有尊严的小猫。张爱玲或许是运用这种手法塑造恐怖异化形象在于“引起我们恐惧和怜悯”,并表达作为女性作家感受到的女性世界。女性异化成没有生命的物体,——“白鸟”、“蝴蝶”取其丧失飞翔能力,没有生命力,失落自主空间的隐喻,表达铁闺阁中形同被幽禁的女性身体。这就是“现代文明”时代女性的形象。正如张爱玲在《茉莉香片》一文中对冯碧落形象的描述:“她不是笼子里的鸟。笼子里的鸟,开了笼,还会飞出来。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张爱玲用“绣在屏风上的鸟”来比喻身在宗法父权社会的女性的悲哀,老旧的生活在消解了女人的生存独立性,蚕蚀了女性的反抗心理,使她们身不由己地奴化成为男性世界的牺牲品,成为思想和心灵上真正的行尸走肉。而“蜘蛛”的运用,则暗示恐怖与反扑力量的酝酿。用猫来暗示女人的动物性本能或宠物的地位,令人感受到女人生命的变幻莫测。“红粉骷髅”暗示了鬼魅似的存在,暗示了邪恶、恶毒的力量。张爱玲小说女主人公身上的所物化的物体都是主人公的气质和悲剧命运的底蕴,是她们的秉性,是虚空的。张爱玲这样创作的目的是用令人恐怖的形象来表达她对女性生存现状的否定。在男性的符号系统中,女性往往是被异化的,她空有人形象而不具备人性,行尸走肉的女性自我被淹没于无符号的混沌大海。张爱玲选择了“物化”并凸现女性的丑陋。在她一系列以女人为主角的小说里,女人的存在常常只是徒具表象、躯壳、外表而不具有真正的人生和人性。
2冷漠的口吻
张爱玲的小说向世人呈现了其独特的女性意识感悟,她在塑造人物、解读女性命运时,往往将自己深深地隐藏在平淡的文字里,用平静得近似冷漠的口吻,甚至怀着嘲弄的微笑叙述着笔下人物的悲剧故事。“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是张爱玲对其小说人物命运的高度概括,也是对在当时社会中讨生活的女性人生的最终诠释。张爱玲是在用一种远距离的、疏离的状态来从事创作,故而呈现出“永远站在潮流外”的冷静和自觉,使她能摆脱“女性被害者”的愤怒情绪,取得了抒写的较佳视点。
在对人性的描写上,张爱玲选择了采用西方作家常用的表现方式——通过展示人性丑陋与邪恶,促使读者对女性本体作出理性的、内在的审视与反思。在她的笔下,几乎没有一个完美的女性,尽管每个女性都有其可取的地方;几乎没有一段美好的姻缘,尽管有个别女性经过重重磨难,最终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婚姻;几乎没有一个心理健康的女性能作为人自主的存在,尽管她也许掌管了经济大权、占据了家长地位。作为女性中的一员,她对女性的悲惨遭遇漠然视之,对女性的缺点却不依不饶,连一点细微的地方也要曝光出来,进行无情的解剖和鞭鞑。张爱玲感受生活的视角是与她独特的生活经历及她的创作个性紧密相关的。她在生活中对男性自私、虚伪本性的清醒体察,对女性生存的艰难和深切的痛苦感受,再加上来自幼年心理上所受的创伤的投影,构成了她感受外部世界的心理基础,自然也就形成了她对女性独特的视角和冷漠的笔触。
张爱玲一生孤僻冷漠,不喜与人交往。除了和她的姑姑、女友炎樱等少数几个人较为投机外,连她弟弟、书迷都不爱理睬,晚年更是一个人孤零零地死在远在美国的洛杉矶家中。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曾指出:“凡是以自我为中心,受自我奴隶压制的作家都有一种为那些气量宽宏、胸怀阔大的作家所不具备的力量,它能把他们心灵所熔铸的形象原原本本地描摹出来,而且还具有自己独特的美,独特的力量,独特的视角。”张爱玲就是这样一位作家。也就是说,作家必须能够站在笔下人物的立场,和他们达成一定的“心灵相通”才能够创造出深刻的艺术形象来。张爱玲的小说作品大多数取材于现实生活,在生活中都是有原型的。张爱玲在谈到原型与虚构、生活与艺术的关系时曾说道:“在西方近人有这句话:一切好的文艺都是传记性的。当然实事不过是原料,我是对创作苛求,对原料非常爱好,并不是尊重事实,是偏嗜它特有的一种韵味,其实也就是人味。”由此可见其小说创作时对人生味和人生真实体验的偏好。如果她不是生活在那样的年代、那样的环境之下,她也不可能写得出这么真实和感人的作品来。正因为张爱玲自身有深切的体会,所以她放弃了当时的主流文学表现形式,选择了自己熟悉的题材,用她刻薄准确的语言,“冷眼看戏”的姿态,真实再现了“五四”前后几十年凡俗女子在生活中的挣扎史。也正是她冷漠无情地对女性命运深刻、真切的剖析,其作品才有一种强烈的震撼力。
3独特的视角
“冷眼看戏”的张爱玲通过对挣扎在世俗生活中的女性形象的否定书写,以及女性在万恶的封建社会的压制下形成的劣根性的深刻审视,远距离地阐述了女性悲剧的必然性,从而形成了她解读、感受和书写的独特视角。
张爱玲总是试图站在人类生存命运的高度来关注人生和人性,因而她对女性有着更深的认识。应该说张爱玲选择的创作角度是新颖的、独特的,尤如一股清风沁入当时主流文学充斥的文坛。张爱玲的作品的独特视角、鲜活生动的描写,与当时被政治窒息了创造力的主流文学的那种毫无个性,大讲技巧的作品相比,更贴合民众。在许多作家都在痛斥敌伪,歌颂未来的光明和美好,憧憬着被解放之后女性的新生活时,她却将笔墨泼洒在表现女性的不幸遭遇和揭示她们自身的劣根性上。《金锁记》里歹毒刻薄的曹七巧、《十八春》里的“红粉骷髅”曼璐等原来都是青春活泼、心理健康的女性,在经历了社会对她们的迫害和不公正待遇之后,她们也蜕变成了“欺压同性”的刽子手,变本加厉地将痛苦付诸在同性身上;《倾城之恋》中忙于找人嫁的流苏、宝络,《连环套》中为了生计与人姘居的霓喜等,把婚姻当作了自己的求生的唯一职业,甘愿受男人的摆布;《红玫瑰与白玫瑰》中自艾自怜的孟烟鹂、《小艾》中忍气吞声的五太太、《太太万岁》中的克已待人的陈思珍,为了极力维护自己的原配地位,完全丧失了一个人活着应有的骨气和尊严;而《十八春》里美丽懂事的曼桢、《多少恨》中自强自立的虞家茵、《沉香屑——第一炉香》中求学上进的葛薇龙等,这些受过教育,自尊自强、自信自立的女孩,按理说,她们应该能摆脱传统观念和道德的束缚,摆脱对男性的依附,选择过一种正常的生活,然而张爱玲笔锋一转,却给她们安排了更为可悲的下场:由于社会的黑影、金钱的诱惑、亲人的迫害,她们不但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最后连亲情、爱情和尊严都保不住,心甘情愿地依旧过着和旧式女性一样的生活。张爱玲对她那个时代的女性既无情地批判旧意识、旧观念对她们的残害,又憎恨她们的自轻自贱。因此,张爱玲笔下各式各样的女性都逃不出这样的宿命的轮回:她们就像一只只绣在屏风上的鸟,没有知觉,没有自由,没有思想,没有出路,待到“年深日久,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她死在屏风上了。”看张爱玲的作品,常常可以感受到隐伏在后面的那种对人生的绝望,冷淡的叙述里往往有力透纸背的悲凉。
综上所述,张爱玲在她的作品中用“冷眼看戏”的姿态,刻薄冷漠的口吻着重表现了女性的阴暗、丑陋与“人性恶”。她尖刻地揭示了女性的不幸遭遇和女性自身的劣根性,无情地剖析了女性悲剧命运的内因,却没让人看到她们的出路以及她们对现实环境的任何改变,这些女性只是处在幻灭与空虚的重压下,上演着一幕幕人生悲剧,而不是积极寻求自我解放的出路,这不仅仅是因为产生于这种时空背景,打上了时代的印迹,更重要的是掺杂了作家本人在个人身世背景上所形成的人生经验,造就了她这个独特的创作个体、独特的个人经历,从而形成了其致力于剖析人性恶的偏执文艺观。张爱玲笔下的女性都很好地体现出作者的人生观,那就是女性“生存的恐慌”,这不仅是物质上而更是精神上的恐慌。在她的小说《封锁》中有这样一句重复了多遍的民谣:“可怜啊可怜,一个人啊没钱!”生存的恐慌威胁着她们,也许,这恐慌也长期威胁着作者,而她笔下的女性只不过是她的一个个代言人,借这些主人公通过作品说出自己内心的话语。张爱玲的人生遭遇,形成了她偏狭的心理定势和“失落者”的心态。正如夏志清教授所说:“张爱玲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可同时又是一个活泼的讽刺作家,记录近代中国都市生活的一个忠实而又宽厚的历史家。”还说“张爱玲的讽刺并不惩恶劝善,它只是她的悲剧人生观的补充。”
[关键词]丑陋;冷漠;独特的视角
[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656(2007)01-0069-04
《流言》、《传奇》是张爱玲的两部作品集,在读者眼前展现了女性特有的形形色色的生命形态。她以女性特有的敏感,去感受都市中女性的生活,描写各式女性的命运,她的笔犹如犀利的解剖刀指向了女性心理,不动声色地向世人揭示了女性心灵充满愚昧、变态的一角,从而呈现出女性孤独、渺小,甚至猥琐、丑陋、无奈的生命原生态。一个女性作家如此诋毁女性,把女人写的如此自私、卑琐、愚昧、变态、贪恋物质,原因何在?有人曾这么说:“看似对男性否定的女性品德进行夸张丑化好似是在狠狠的鞭笞,其实是以退为进,刻意压低女性的声音,以显示男性文化对女性的暴力”。本人认为张爱玲以其独特的女性描写模式,从女性心理、生理两方面揭示出女性在以父权制为中心的文化传统中备受压抑的处境,并从女性深层心理结构上去挖掘其自身的痼疾及其文化根源,凸显女性的人生信念。本文试从张爱玲对女性形象丑陋的的刻画,冷漠的口吻,及独特的视角等几个方面的进行论述。
1丑陋的刻画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对女性形象的刻画落笔在人性深处的阴暗、自私、虚伪、孤独、冷漠。通过张爱玲的作品,我们触摸到了“人性恶”的一面,人的灵魂阴暗与丑陋的一角。张爱玲笔下的人物苍白、渺小,没有高尚的情操,没有善良的心,也没有质朴、憨厚的性格。他们在兽欲、生物性、习俗的挤压下沉沦。中国女性对男性的从属观念经过几千年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残暴的压制,使许多女性自觉地奴化和物化,甚至以此为满足。备受压抑与服从已成为女性的一种生存的习惯。张爱玲毫不留情地拭去所有的粉饰,用冷酷的笔调描述了女性被奴化和钳制的生存状态,她笔下的女性在社会的重压下,心灵被扭曲,性格被异化。
1.1对女性固有“奴性”的否定
自从进入男权社会,中国女性就逐步被规定在小家庭的范围内,恪尽妇人之道,承担着生儿育女、相夫教子之职。由于女性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小,使得她们终日被封闭在与世隔绝的小环境中,个性慢慢散失,这就造成了女性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生活上处处依赖男人,落入了“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的可悲境地。女人想要通过婚姻来抵制生存的威胁,而婚姻在张爱玲笔下是无爱的,“有爱的婚姻是痛苦的”,但婚姻又受不了爱的诱惑。婚姻是枷锁,妄想用它来锁住别人,锁住爱情,都是不可能办到,结果只能毁了自己。腐朽的没落文化封锁住男女间的情爱,美好的情爱被禁锢,被异化,当枷锁打开时,真实的原欲才纷纷现出本来面目,率真自然的感情才得以迸发。
对于未出嫁的女子而言,张爱玲描写的是一部部真真实实的嫁人录。未出嫁的女子都千方百计地要去寻觅一个有钱的男人嫁了,便等于找到了终身寄托,这辈子就有了依靠。《金锁记》里的姜长安遇到从德国归来的章世舫时,才见第一面,便芳心暗许;《倾城之恋》中的离异待嫁的流苏与二十四岁未出阁的宝络、急于找婆家的金枝、金蝉,为吸引范柳原的注意力,更是斗智斗勇,使出浑身解数,目的就是要拴住这个男人的心;《红鸾禧》中的邱玉清以及她的五个装腔作势、卖弄风骚的表妹们,为了吸引男性的注意力更是丑态百出。
对于已成家的女子而言,也不是一帆风顺,高枕无忧的。为了维护自己在家中的地位,为了捍卫自己妻室的身份和头衔,她们忍辱负重、克已待人。《说文解字》中讲道:“妇人,从人者也。”张爱玲写的女性形象无一例外都遵从这条古训。在她笔下的女性虽已走出了旧时代的时光隧道,但她们的心智却还是被困在传统道德和“自我奴化”的囚网中无法自拔。她们为了吸引男性的目光,为了取悦丈夫,竟甘心扮演琐碎、辛苦、卑微、忍让、克己的角色,这就是她们的原生本相,透过这些细节,我们看到的是强悍男性对柔弱女性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人生态度的渗透和支配。
更可悲的是,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大多数是明白自己的处境而自甘堕落,从心理上把自己当作男性的附庸的。恩格斯在谈到被压迫者的生活态度时说过:“只要他们还对统治阶级感到愤怒,他们就仍然是人;但如果他们乖乖地让把挽轭套在脖子上,又想把挽扼下的生活弄得比较过得去一点,而不想摆脱这个挽轭,那他们就真的变成牲口了。”张爱玲笔下的中国老式女儿们在千年传统道德的束缚下,自觉或不自觉地奴化成了“挽轭”下的“牲口”,没有人的自觉,丧失了女性作为人的权利。她们自身甘心为奴的屈服,正配合了外界环境对她们的不公正压迫,使得女性沦为男性附庸地位的接力棒代代相传。
1.2女性形象的物化
在张爱玲小说中注重了人物丑陋的刻画,常给女主人公附上物性。如在《花凋》中郑川嫦在作者眼中是“冷而白的白大蜘蛛”,川嫦则认为自己是没有灯的灯塔;《半生缘》中顾曼璐是“红粉骷髅”;《茉莉香片》中冯碧落是“屏风白鸟”;《金锁记》中七巧是“蝴蝶标本”;《小艾》中小艾也像一只淡漠具有尊严的小猫。张爱玲或许是运用这种手法塑造恐怖异化形象在于“引起我们恐惧和怜悯”,并表达作为女性作家感受到的女性世界。女性异化成没有生命的物体,——“白鸟”、“蝴蝶”取其丧失飞翔能力,没有生命力,失落自主空间的隐喻,表达铁闺阁中形同被幽禁的女性身体。这就是“现代文明”时代女性的形象。正如张爱玲在《茉莉香片》一文中对冯碧落形象的描述:“她不是笼子里的鸟。笼子里的鸟,开了笼,还会飞出来。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张爱玲用“绣在屏风上的鸟”来比喻身在宗法父权社会的女性的悲哀,老旧的生活在消解了女人的生存独立性,蚕蚀了女性的反抗心理,使她们身不由己地奴化成为男性世界的牺牲品,成为思想和心灵上真正的行尸走肉。而“蜘蛛”的运用,则暗示恐怖与反扑力量的酝酿。用猫来暗示女人的动物性本能或宠物的地位,令人感受到女人生命的变幻莫测。“红粉骷髅”暗示了鬼魅似的存在,暗示了邪恶、恶毒的力量。张爱玲小说女主人公身上的所物化的物体都是主人公的气质和悲剧命运的底蕴,是她们的秉性,是虚空的。张爱玲这样创作的目的是用令人恐怖的形象来表达她对女性生存现状的否定。在男性的符号系统中,女性往往是被异化的,她空有人形象而不具备人性,行尸走肉的女性自我被淹没于无符号的混沌大海。张爱玲选择了“物化”并凸现女性的丑陋。在她一系列以女人为主角的小说里,女人的存在常常只是徒具表象、躯壳、外表而不具有真正的人生和人性。
2冷漠的口吻
张爱玲的小说向世人呈现了其独特的女性意识感悟,她在塑造人物、解读女性命运时,往往将自己深深地隐藏在平淡的文字里,用平静得近似冷漠的口吻,甚至怀着嘲弄的微笑叙述着笔下人物的悲剧故事。“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是张爱玲对其小说人物命运的高度概括,也是对在当时社会中讨生活的女性人生的最终诠释。张爱玲是在用一种远距离的、疏离的状态来从事创作,故而呈现出“永远站在潮流外”的冷静和自觉,使她能摆脱“女性被害者”的愤怒情绪,取得了抒写的较佳视点。
在对人性的描写上,张爱玲选择了采用西方作家常用的表现方式——通过展示人性丑陋与邪恶,促使读者对女性本体作出理性的、内在的审视与反思。在她的笔下,几乎没有一个完美的女性,尽管每个女性都有其可取的地方;几乎没有一段美好的姻缘,尽管有个别女性经过重重磨难,最终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婚姻;几乎没有一个心理健康的女性能作为人自主的存在,尽管她也许掌管了经济大权、占据了家长地位。作为女性中的一员,她对女性的悲惨遭遇漠然视之,对女性的缺点却不依不饶,连一点细微的地方也要曝光出来,进行无情的解剖和鞭鞑。张爱玲感受生活的视角是与她独特的生活经历及她的创作个性紧密相关的。她在生活中对男性自私、虚伪本性的清醒体察,对女性生存的艰难和深切的痛苦感受,再加上来自幼年心理上所受的创伤的投影,构成了她感受外部世界的心理基础,自然也就形成了她对女性独特的视角和冷漠的笔触。
张爱玲一生孤僻冷漠,不喜与人交往。除了和她的姑姑、女友炎樱等少数几个人较为投机外,连她弟弟、书迷都不爱理睬,晚年更是一个人孤零零地死在远在美国的洛杉矶家中。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曾指出:“凡是以自我为中心,受自我奴隶压制的作家都有一种为那些气量宽宏、胸怀阔大的作家所不具备的力量,它能把他们心灵所熔铸的形象原原本本地描摹出来,而且还具有自己独特的美,独特的力量,独特的视角。”张爱玲就是这样一位作家。也就是说,作家必须能够站在笔下人物的立场,和他们达成一定的“心灵相通”才能够创造出深刻的艺术形象来。张爱玲的小说作品大多数取材于现实生活,在生活中都是有原型的。张爱玲在谈到原型与虚构、生活与艺术的关系时曾说道:“在西方近人有这句话:一切好的文艺都是传记性的。当然实事不过是原料,我是对创作苛求,对原料非常爱好,并不是尊重事实,是偏嗜它特有的一种韵味,其实也就是人味。”由此可见其小说创作时对人生味和人生真实体验的偏好。如果她不是生活在那样的年代、那样的环境之下,她也不可能写得出这么真实和感人的作品来。正因为张爱玲自身有深切的体会,所以她放弃了当时的主流文学表现形式,选择了自己熟悉的题材,用她刻薄准确的语言,“冷眼看戏”的姿态,真实再现了“五四”前后几十年凡俗女子在生活中的挣扎史。也正是她冷漠无情地对女性命运深刻、真切的剖析,其作品才有一种强烈的震撼力。
3独特的视角
“冷眼看戏”的张爱玲通过对挣扎在世俗生活中的女性形象的否定书写,以及女性在万恶的封建社会的压制下形成的劣根性的深刻审视,远距离地阐述了女性悲剧的必然性,从而形成了她解读、感受和书写的独特视角。
张爱玲总是试图站在人类生存命运的高度来关注人生和人性,因而她对女性有着更深的认识。应该说张爱玲选择的创作角度是新颖的、独特的,尤如一股清风沁入当时主流文学充斥的文坛。张爱玲的作品的独特视角、鲜活生动的描写,与当时被政治窒息了创造力的主流文学的那种毫无个性,大讲技巧的作品相比,更贴合民众。在许多作家都在痛斥敌伪,歌颂未来的光明和美好,憧憬着被解放之后女性的新生活时,她却将笔墨泼洒在表现女性的不幸遭遇和揭示她们自身的劣根性上。《金锁记》里歹毒刻薄的曹七巧、《十八春》里的“红粉骷髅”曼璐等原来都是青春活泼、心理健康的女性,在经历了社会对她们的迫害和不公正待遇之后,她们也蜕变成了“欺压同性”的刽子手,变本加厉地将痛苦付诸在同性身上;《倾城之恋》中忙于找人嫁的流苏、宝络,《连环套》中为了生计与人姘居的霓喜等,把婚姻当作了自己的求生的唯一职业,甘愿受男人的摆布;《红玫瑰与白玫瑰》中自艾自怜的孟烟鹂、《小艾》中忍气吞声的五太太、《太太万岁》中的克已待人的陈思珍,为了极力维护自己的原配地位,完全丧失了一个人活着应有的骨气和尊严;而《十八春》里美丽懂事的曼桢、《多少恨》中自强自立的虞家茵、《沉香屑——第一炉香》中求学上进的葛薇龙等,这些受过教育,自尊自强、自信自立的女孩,按理说,她们应该能摆脱传统观念和道德的束缚,摆脱对男性的依附,选择过一种正常的生活,然而张爱玲笔锋一转,却给她们安排了更为可悲的下场:由于社会的黑影、金钱的诱惑、亲人的迫害,她们不但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最后连亲情、爱情和尊严都保不住,心甘情愿地依旧过着和旧式女性一样的生活。张爱玲对她那个时代的女性既无情地批判旧意识、旧观念对她们的残害,又憎恨她们的自轻自贱。因此,张爱玲笔下各式各样的女性都逃不出这样的宿命的轮回:她们就像一只只绣在屏风上的鸟,没有知觉,没有自由,没有思想,没有出路,待到“年深日久,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她死在屏风上了。”看张爱玲的作品,常常可以感受到隐伏在后面的那种对人生的绝望,冷淡的叙述里往往有力透纸背的悲凉。
综上所述,张爱玲在她的作品中用“冷眼看戏”的姿态,刻薄冷漠的口吻着重表现了女性的阴暗、丑陋与“人性恶”。她尖刻地揭示了女性的不幸遭遇和女性自身的劣根性,无情地剖析了女性悲剧命运的内因,却没让人看到她们的出路以及她们对现实环境的任何改变,这些女性只是处在幻灭与空虚的重压下,上演着一幕幕人生悲剧,而不是积极寻求自我解放的出路,这不仅仅是因为产生于这种时空背景,打上了时代的印迹,更重要的是掺杂了作家本人在个人身世背景上所形成的人生经验,造就了她这个独特的创作个体、独特的个人经历,从而形成了其致力于剖析人性恶的偏执文艺观。张爱玲笔下的女性都很好地体现出作者的人生观,那就是女性“生存的恐慌”,这不仅是物质上而更是精神上的恐慌。在她的小说《封锁》中有这样一句重复了多遍的民谣:“可怜啊可怜,一个人啊没钱!”生存的恐慌威胁着她们,也许,这恐慌也长期威胁着作者,而她笔下的女性只不过是她的一个个代言人,借这些主人公通过作品说出自己内心的话语。张爱玲的人生遭遇,形成了她偏狭的心理定势和“失落者”的心态。正如夏志清教授所说:“张爱玲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可同时又是一个活泼的讽刺作家,记录近代中国都市生活的一个忠实而又宽厚的历史家。”还说“张爱玲的讽刺并不惩恶劝善,它只是她的悲剧人生观的补充。”
温馨提示:内容为网友见解,仅供参考
无其他回答
相似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