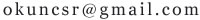,《倾城之恋》的色调更接近于作家的创作底色,它透过貌似罗曼蒂克的爱情,展示人生简单而又真切的本相,最后达到对人性的一种富于哲学意味的思考,具体在小说中又是通过对爱情心理程式的描写体现出来的。在这篇小说中,作家对爱情心理程式的演绎描写得颇费心智,对于这一点,我们过去注视不够。我认为,这是解读《倾城之恋》的关键。本文试图从这一角度对《倾城之恋》进行解读。 白流苏和范柳原的爱情角逐是整个小说的中心线索。而白流苏则又是使这场戏上演并发展的关键人物,她貌似被动的地位与她隐藏的控制力量形成了一种张力,正是这种张力构成的磁场把范柳原给吸住。但从白流苏的角度来说,这又不能仅仅理解为是某种“诱惑”技巧的使用,吸引范柳原的是从白流苏的个性以及她对生活的领悟中自然流泻出来的生活态度和方式。技巧是外在的,而这里的张力却来自于内在的魅力。 男女之间的爱情纠葛通常被认为是“两个人之间的战争”,“两个人之间的战争”有各种各样的模式,其中“爱情程式”对这种模式有重大的影响。在《倾城之恋》中,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爱情程式是一种接纳与拒绝、肯定与否定交替出现的方式,这是一个呈螺旋式规律上升的爱情程式。“战争”是第一个回合:离弃后的白流苏住回娘家,受到势利的家人的排挤。困境中的白流苏这时遇上了前来与妹妹相亲的华侨富商范柳原,并以迷人的东方情调吸引了范柳原,“难得碰见你这样一个真正的中国女人”。于是,范柳原邀请二十八岁的离异少妇白流苏离开上海,来到了香港。这是白流苏与范柳原之间的第一次接纳和肯定。从形式上来看,范柳原是主动的,白流苏只是做了被动的响应。但若把人的地位丢开,从产生“一见钟情”的施予方与被施予方的角度考虑,白流苏才是主动的。当然这远远只是开始。就流苏目前的状况,想一下子就完全抓住花花公子的范柳原是不可能的。但既然命运给了流苏这么一次机会,她就得冒险试上一回。 初到香港,白流苏对范柳原尽管也有不满,但“因为交情还不够深,没有到吵嘴的程度”,只得先委屈一下自己。在香港的游玩中,随着了解的加深,流苏敏感、矜持、孤傲的性格也逐步显露出来,而柳原则对流苏的依恋进一步加深,在浅水湾的那一堵墙下,他对流苏说: “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柳原的这种伤感的末世情绪,是不会轻易地向他人抒发的。流苏点燃了他心中未曾熄灭的人性之光,所谓“生死契阔,与子相悦”的这种古典的爱情是能打动几乎所有人的。尽管这种爱情已在渐渐地远去,但人们在梦中都会依稀为它保留一块位置,无论是为了生存的白流苏,还是为了玩乐的范柳原。随着两人渐渐熟悉,流苏也少了些许矜持。只有一次,两人在海滩玩互相在对方身上劈劈啪啪打沙蝇时,流苏却突然被得罪了,这显然不完全是柳原的过错,流苏气的是自己,是对自己这一放任的行为的否定。由于这一不雅的举动,不仅使她优雅的古典气质破坏殆尽,更使她恼火的原因还在于她有一种没有得到对方却被对方占了便宜的羞辱。流苏不愧是一个十分聪明的女人,她的这一“被得罪”不仅使自己的面子得到某种挽回,同时还把错误转嫁给对方,给自己留下了回旋的余地。这是流苏对柳原的第一次拒绝,女人能够生气毕竟是有了地位的象征。 第二个回合:这是白流苏的地位和处境发生变化的关键回合。此时的白流苏很清醒她的境地,“他要她,可是他不愿意娶她”,因为在范柳原看来,白流苏作为破落的望族小姐是不得不依附于他的经济实力的,因而不愿正式娶她而只愿把她当情妇。尽管这时柳原已主动和她言和,但此次被动的却是她自己:“她早不同他好,晚不同他好,偏拣这个当口和他好了,白牺牲了她自己,他一定不承情,只道她中了他的口计。”更让流苏难堪的是柳原有意当着人做出亲狎的神气,这似乎让流苏势如骑虎,除了做他的情妇没有第二条路。然而流苏毕竟是流苏,她知道:“如果迁就了他,不但前功尽弃,以后更是万劫不复了。她偏不!就算她枉担了虚名,他不过口头上占了她一个便宜。归根结底,他还是没得到她。既然他没有得到她,或许他有一天还会回到她这里来,带了较优的议和条件。”因而便义无反顾地决定回上海。范柳原对此也没有任何强烈的反应,可以看出范柳原在这两个回合中的反应似乎是迟钝的,因为“他拿稳了她跳不出他的手掌心去”。第二个回合从接纳到拒绝转换得很快,对流苏来说,既然她仍然处于受制于人的境地,不如索性以退为进。起码,柳原还是在乎她的。她也只有这惟一的赌注了。没有这场赌,她便赢不来她所想要的全部。 第三个回合:回沪后的流苏不愿自贬身价外出就业,在家苦捱着日子,只等着范柳原的一声召唤。她很清楚,她目前艰难的经济状况、个人生活状况的解决都维系于这一声召唤。流苏的冒险离去,实在有一种孤注一掷的味道。离去最终是为了回去。最后的结果当然如她所愿,尽管范柳原的一张让她回港的电报又使她自尊受挫,使流苏有一种失败的感觉,因为按照她自己的心性,她是不会这么快就屈服的,“内中还搀杂着家庭的压力--最痛苦的成分”,但还有什么力量能与生存的需要相比呢?而且从某种意义来说,这也是她计划的题中应有之义,并没有多少突兀的成分,重新回到范柳原身边于是顺理成章。尽管这一次的相聚是短暂的:范柳原随即就要动身去英国,也没有给她的地位带来实质性的改变,但起码在流苏看来她得到了两方面的好处:她拼命抓住范柳原,首先是经济上的安全,这个目的看来已经达到了。至于和范柳原的将来,也并不是没有希望:“柳原是一个没长性的人,这样匆匆地聚了又散了,他没有机会厌倦她,未始不是于她有利的。一个礼拜往往比一年值得怀念。”正因为流苏深谙爱情或者说人性的真谛,这一次表面上是柳原主动离去,使得流苏不再充当拒绝者的角色,但在经历了这几次曲折后,读者会和流苏一样期待着后面的故事。 小说的结局打破了这种循环,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这一次不再是流苏智取,而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把柳原拉回到她的身边,并使得流苏的心愿成为现实。任何人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想像:如果没有这场战争,它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又以何种方式结尾呢?当然,张爱玲不是我般俗辈,她有着更高明的安排。所谓“倾城之恋”不仅是为了给小说以一个奇峰突起的情节设置,使故事悖离读者的阅读期待,更重要的是作者由此而使小说所关注的生存主题由隐而显地凸现出来,并使小说的思想容量大大增强了。 在小说中,爱情是作为人的一种生存形态而存在的,因为仅仅写爱情或透过爱情写生存确实是不同的两种境界。 “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白流苏显然一直考虑的是生计问题,通过一种摇摆不定的爱情模式,她获取了生活的保障。如果不是因为生存的压力,流苏会使自己在这一爱情程式中的表现更加出色,因为毕竟在她看来,柳原还是可爱的,他给她美妙的刺激。这也就意味着流苏对柳原的认同并不完全出于经济的考虑,是生存的压力迫使她的行为发生了偏离(如第二回合)。范柳原这个明显兼顾了人性的优点和弱点的人,他在小说中的语言透露着他在人性的两种境界之间徘徊的矛盾和痛苦。从浅水湾的那堵墙下的感伤到旅馆里的电话表白,都不是一般地谈情说爱,而是人性的无奈的展示。可以说,小说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对人的一般性生存的关注,玫瑰色的面纱无论如何美丽,也不会喧宾夺主。正如作者所评价的:“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 由于已经涉及到爱情与存在的关系,西美尔的两性理论可以为这篇小说打开更新一层次的境界。他认为,“大量一般性的人类行动形式正是在两性关系的行为方式中找到了其规范性例证”,“在这些行为摇摆的二元性中,呈现出拥有或没有的那些经常无法回避的基本关系”②。由此,《倾城之恋》的爱情角逐并不仅仅止于以上所说,它有着更隐蔽的含义。白流苏在爱情方式上的不断重复的接纳与拒绝,构成了人的一般生存状态的原型。也就是说,人在生存中与现实构成的这种关系都如这种普遍的爱情程式一样,都表现为一种不断的拥有和失去的基本关系。这里包括我们所执著的事业,也包括我们每个人的个人信仰,还包括我们每天处理的日常事务,当然也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自然界的现象也莫不如此。这是整个宇宙共有的生命规律。人总是被两种完全相反的力量作用着,它们一方面是刘‘立的,另一方面又在彼此相互寻找、相互补充。爱情也好,日常生活也好,它们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 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白流苏何以既懂得爱情心理学,也懂得生存的一般定律。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倾城之恋》并不是一般的爱情小说,而是一篇关于人的存在哲学的小说。白流苏和范柳原的关系的“肯定和否定、给和拒绝的神秘交错”③,实际上已没有任何现实的意义,它们只是可任意置换的符号,可替换成人在生存中的无数两极对立的因素,在它们的作用下,人们的行为表现为一种同时性地抓住和放弃,这里没有完全的拥有和失去,抓住是为了再次放弃,放弃是为了再次抓住。它遍布在人们生活的每一个地方,这是一个没有终点的旅程。“这种形式正是在两性关系中得到了最典型和最完美的体现,而这种关系自身已经将生活中或许最黑暗和最具悲剧性的关系,隐藏在生活最令人陶醉和最魅力四射的形式背后。”④即使白流苏最后得到了范柳原,但依照西美尔的观点,这种拥有同时又意味着没有。因为在形而上学意义上人最终都是孤独的,一方对另一方的喜欢,只不过是一条通向无止境的道路。所以当初柳原哀恳流苏“我要你懂得我”时,心里是绝望的。而当流苏与柳原成亲后,柳原不和她闹着玩了,“他把她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那是值得庆幸的好现象,表示他完全把她当作自家人看待--名正言顺的妻。然而流苏还是有点怅惘。”白流苏不会认为她是胜利者,范柳原也不一定就是失败者。张爱玲借女主角上演的这出戏,实在是道破了两性之间爱情关系的精髓。西美尔说这是一种悲剧性的人生形式,实在不为过。张爱玲的所谓“苍凉”也意在于此吧!
温馨提示:内容为网友见解,仅供参考
第1个回答 2013-07-02
《倾城之恋》作为小说的标题,首先给人一个阅读的提示。我们读小说,总是从标题开始的,标题唤起读者一些可能的阅读经验,是作者预先设计的读者期待视野。如果这个说法不错的话,我们可以设想,张爱玲在拟定这个题名时期待读者首先会赞成,这里将讲述一段传奇——“罗曼司”,即一段动人心魄的爱情故事。就此而言,在标题范围内,“倾城之恋”不具有叙事性质,只是一个复合名词,在文学语汇的传统中,它是一个形容词。形容妇女容貌极美,美到令众多的人倾慕、倾倒的程度。“倾城倾国”一词,语本《汉书·外戚传》:“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齐梁时期钟嵘在《诗品》中论及诗之吟咏性情的功能时也写道:“……女有扬娥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1]
据此,女有美色,倾城倾国,一旦进入文学叙事,显然就要暗示一个非凡的结果。“汉皇重色思倾国”,引出白居易的《长恨歌》,创造了一个千古爱情的传奇。
但是,读完了张爱玲的这篇小说,就会发现,说它是传奇,不如说是一个反传奇的故事。书中的女主人白流苏并不是美貌惊人,流苏与范柳原成婚,交易的因素亦多于爱情的因素。倒是在“倾城”的另一意义上:倾覆、倒塌,沦陷,在这个意义上,倾城之恋名副其实。香港的沦陷成全了白流苏和范柳原,使他们做成了一对平凡的夫妻。
显然,这一结局的实际指涉对读者可能的期待是一个倾覆。不妨由这里入手,探讨这个倾覆带来的意义的游移、空缺或潜层的增殖。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据此,女有美色,倾城倾国,一旦进入文学叙事,显然就要暗示一个非凡的结果。“汉皇重色思倾国”,引出白居易的《长恨歌》,创造了一个千古爱情的传奇。
但是,读完了张爱玲的这篇小说,就会发现,说它是传奇,不如说是一个反传奇的故事。书中的女主人白流苏并不是美貌惊人,流苏与范柳原成婚,交易的因素亦多于爱情的因素。倒是在“倾城”的另一意义上:倾覆、倒塌,沦陷,在这个意义上,倾城之恋名副其实。香港的沦陷成全了白流苏和范柳原,使他们做成了一对平凡的夫妻。
显然,这一结局的实际指涉对读者可能的期待是一个倾覆。不妨由这里入手,探讨这个倾覆带来的意义的游移、空缺或潜层的增殖。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相似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