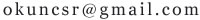张爱玲小说的语言艺术
张洁
[摘要] 张爱玲作为一个从40年代就大红大紫的女作家,她的作品一直倍关注。她的作品被傅雷称为“我们文坛上最美的收获之一。”张爱玲的小说不仅在人性方面有深刻入微的挖掘,表现“压抑的悲哀”相当出色。更另笔者惊叹的是她的语言艺术,可谓出神入化。她的奇巧的比喻,她的诡异的色彩运用,和她的文章里反复出现的各种意象与象征,构成了她精湛的语言技巧。使得她的小说魅力永存,历久长新。
[关键词] 张爱玲;语言;比喻;色彩;意象,象征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独树一帜的、极富传奇色彩的作家,夏志清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里用了四十多页的篇幅为张爱玲正名,到现在,港台旅美作家把张爱玲的创作成就摆在鲁迅、巴金、茅盾等现代名家“等高”的位置上,把她誉为“中国最优秀、最主要的作家之一”。[1] 傅雷先生在1933年所著的《论张爱玲的小说》里曾写到“总而言之,才华最爱出卖人!像张女士般有多方面的修养而能充分运用的作家(绘画、音乐、历史的运用,使她的文章特别富丽动人)……”[2] 虽然在这里傅雷先生是在批评着新生的女作家张爱玲女士,但是实际上也是从另一个侧面间接地肯定了张爱玲作品所体现出来的文学才华。其小说的魅力,不只在于她以一支细致传神的笔精彩地描绘了殖民地香港和沦陷区上海独特的时代风情,也不只在于她那个时代,她执着于自己的世界,抒写普通人的悲欢离合,而更多的在于她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对人生悲剧性的深刻认知,以及她在作品中所表现出的独特的悲剧美。张爱玲的小说不仅在人性方面有深刻入微的挖掘,表现“压抑的悲哀”相当出色,更令笔者惊叹的是她的语言特色,可称出神入化。自从张爱玲于1944年的小说集《传奇》问世之后,便震惊世人,其作品的艺术魅力,激荡人心,特别是她小说所独具的语言更是娴熟、精湛,富有创造力,让人难以忘怀。
一、对形象独特的比喻的偏好
张爱玲是一个有着与众不同个性的作家,她看似世俗,实则超凡脱俗,这一点在她的小说中表现出来就是她对事物独树一帜的敏锐感受,最突出的便是她把这样体验独特的感受运用恰到好处,极具艺术感染力的比喻外化出来。在她的作品里,从不吝啬使用比喻,似乎万事万物皆可拿来做比喻,就连很多别人已经写过、写滥的事和物在她的笔下,也突然就与其他事物发生了联系,变成了绝妙的比喻,变成了她任意驱使表达爱憎的工具,就像她最经典的那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让人禁不住一读三叹,拊掌称妙。在《沉香屑 第一炉香》里她曾写到“薇龙那天穿着一件磁青薄绸旗袍,给他那双绿眼睛一看,她觉得她手臂像热腾腾的牛奶似的,从青色的壶里倒了出来,管也管不住,整个的自己全泼出来了。”这是一段以热牛奶比喻女人臂膊之洁白美丽的绝妙描写。在一般人的概念里,固体的手臂再白,却与液状的牛奶毫不相干,两者的差距不言而喻,只有一点“白”是相似的。写女人肌肤嫩白的比喻又何止千种万种,却从来没有人把这样的肌肤之白比作自己往外泼的牛奶。这样的描写既通过读者的视觉来让人感受乔琪的色迷心窍、蠢蠢欲动的形象,又表现了薇龙的竭力自持却又虚荣不能自拔的心态。张爱玲的话语止于此处,似乎只小小的比喻,略有点通感的意味,但是却于其中又蕴涵深幽绵远的暗示,这种暗示似无却有,把作者想说又不必说出、把读者能懂但又看不到的话不知不觉地说了出来,好像是张爱玲的不经意的一个眼神过来,就让读者随即体会了她在此细微的感觉,完成了作者与读者之间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里的交流。
张爱玲的话语不但是独特的,而且相较于其他作家而言,更近似于“恶毒”,许多通常人们以为美的事物、善的事物,在她的笔下都和我们的日常经验发生了扭转性的变化,有时让人读后瞠目结舌。似乎在她的世界里,白雪公主也有如狼外婆般丑陋的时候,但是正是这种“恶毒”的比喻,她的温和的话语更能一语中的,深刻地反映出事物的本质来。并且这样的比喻下,讽刺变得鲜明起来,幽默也将更加凸显。
张爱玲在香港读书期间,她的表姊在上海去世了。听闻这个消息,张爱玲很是悲痛,后来便有了以这个表姊为原型的小说《花凋》。《花凋》里的主人公郑川嫦的父亲郑先生的原型也就是张爱玲的舅父。可是她终究没有给自己的亲人留一点情面:“郑先生是个遗少,因为不承认民国,自从民国纪元起他就没长过岁数。虽然也知道醇酒妇人和鸦片,心还是孩子的心。他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多么恐怖的字眼,就像上层人士不说粗话一样,风雅的文人也决计不会碰触这样的字眼——也许想都无法想到。可是张爱玲这样出人意料地一一写出来,似乎就再也没有比这更贴切的字眼了。郑先生的装腔作态,他的严重的不合适宜在张爱玲残酷的比喻下,一下子现出了原型。而正是这句话,为下文打好了伏笔。郑川嫦在有生之年没有长久幸福过,连死后还要被装点成为家庭的门面,全是因为有这样的父亲,这样的家庭。这就是张爱玲语言的魔力,仅用一个辛辣的讽刺比喻,就统一了整篇小说的背景,推动了所有情节的展开。
但是让比喻之间跳跃着幽默诙谐的音符,也是张爱玲语言的特点。在《花凋》里她也戏谑幽默:“郑太太对孩子说:‘新鞋上糊了这些泥?还不到门口的棕垫子上塌掉它!’那孩子只顾把酒席上的杏仁抓来吃,不肯走开,只吹了一声口哨,把家里养的大狗唤了来,将鞋在狗背上塌来塌去,刷去了泥污。郑家这样的大黄狗有两三只,老而疏懒,身上生癣处皮毛脱落,拦门躺着,乍看就仿佛是一块敝旧的棕毛毯。”看小说看到此处的读者,虽然对于郑先生家的种种已经见惯不怪了,但是这里又突然冒出了一只可以擦鞋的狗,还是让他们不禁莞尔,书中阴沉的气氛也似乎有了亮点,郑家的一切我们也看得更加通透了。
在小说中把常见的意象和画面变得更加生动、活跃、更具风姿,生动地传递本体和喻体之间的共同神韵;把心中的丘壑附在形象的比喻中,用比喻更好地完成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和沟通;用比喻为情节造势,让读者在或惊异或放松的心态下慢慢地走进作者创造的故事中去。这,就是张爱玲的比喻,就是张爱玲的语言艺术。
二、对色彩语言的反义活用的热爱
张爱玲不仅仅是一个作家,正如傅雷先生所说,她具有多方面的才华,还可称得上是一个画家。她的作品就是由一幅幅的画组合而成,由一种种的色彩搭配而成,愉悦的场面她便给加上明快的颜色,压抑的场面她便给加上暗淡的色彩。张爱玲自己也在她的《天才梦》里写到:“对于色彩、音符、字眼我及其敏感。”“我学写文章,爱用‘色彩浓厚、音韵铿锵的字眼’如‘珠灰’、‘黄昏’、‘婉秒’,‘splendour’,’melantholy’,因此常犯了堆砌的毛病。直到现在,我仍然爱看《聊斋志异》与俗气的巴黎时装广告,便是为了这种有吸引力的字眼。”对于色彩,她有着与众不同的见解,总不按常规出牌,不按常理用词,有着鲜明的“张爱玲”特质,这也是她的一大特点。
《鸿鸾禧》里长着团白脸的已婚女人娄太太,不被家人尊重,孤独哀伤,借给未来媳妇做花鞋来解除忧虑。而新娘玉清出嫁前,竟然有一种“决绝的、悲凉的感觉”,结婚进行曲演奏时,‘半闭着眼睛的白色新娘像是复活的清晨还没有醒过来的尸首’。通常意义上穿着白色婚纱的新娘是一个女人一生中扮演的最美丽的角色,张爱玲却比之为令人作呕的毫无人色的尸首,从而前所未有地对传统意义上的纯洁白色进行了创造性的恶意运用。在这白色尸首的映衬下,小说前面大量色彩铺垫便构成了一种无意义,一种反讽。除了“白”,张爱玲的作品中也屡屡出现“红”。《红玫瑰与白玫瑰》更多次写到红色。在振保与娇蕊一夜床第之欢后,张爱玲写到“昨天晚上忘了看看有月亮没有,应当是红色的月牙。”这是虚写。另一次是实写,振保醒来后发现头发里有一弯剪下来的指甲,像小红月牙,那是娇蕊看到自己养的指甲划伤振保后剪下的。此处红色既是实写又是想象,既象征王娇蕊旺盛的生命力和热烈的情感,又有与振保偷情后的愉悦与不安。此后,张爱玲又将“红”与“白”做了一次无人能出其右的对比:“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窗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红色是蚊子血,给了人一种肮脏的感觉,是心口上的朱砂痣,却暗含了一种得不到的痛苦,由此,张爱玲又消解了传统意义上的“红”的内涵。色彩本是一种没有生命的存在,而色彩语言经过作家心灵之光的辐射和审美观照后,就已凝聚了作家的独特个性与生命追求。
在张爱玲的笔下,人生就是色彩,无数的人生就是由五颜六色,千姿百态的色彩构成的,在她的心中,色彩就是人生,色彩里包容了一切她所看到、所知道、所倾诉的百态人生。对读者而言,色彩在张爱玲的小说里不再是一种简单的语言符号,而是她对语言出神入化的把握和摆布,是她对往事、对生活、对情感、对人生、对世界的一种超越和诠释。她赋予色彩以生命,她用色彩表达了另一种情愫,也许这正是她的小说艺术产生了无穷美丽的重要原因,也正是她的小说百读不厌的原因所在。
三、对象征、意象美的执意追求
“一辆衔接一辆,像排了队的小孩,嘈杂、叫嚣,愉快地打着哑嗓子的铃:“克林,克赖,克林,克赖!”——“电车”,这个名词曾经反复出现在张爱玲的文字里:“有时候,电车全进了厂了,单剩下一辆,神秘地,像被遗弃似的,停在街心。”电车最初的意义只是一种穿行于城市的交通工具,一种载体。但在张爱玲的视野里,它逐渐升华为承载生命的容器。正是通过《封锁》的创作,张爱玲开始了对“电车”象征意义的发掘。“如果不碰到封锁,电车的进行是永远不会断的。”电车突然不再在正常的轨道上像往常一样往前走了,那么溢出正常生活轨道之后人会出现一些怎样的问题呢?华茂银行的会计师吕宗桢开始鼓起勇气向身边的吴翠远说话了,只是聊聊,就开始了诉说,慢慢的,在电车这个与外界隔绝的容器里,他开始掉进了自己织的网中,说着说着,忽然就觉得恋爱了,断定了翠远“是一个可爱的女人——白,稀薄,温热,像冬天里你自己嘴里呵出来的一口气。” 想到了他们的结合会牺牲了她的前程。可是终究,“封锁开放了。‘叮玲玲玲玲玲’摇着铃,电车载着吕宗桢回到了家里,而电车上那个女人的脸已经开始模糊,残存的印象只有自己说过的一些话。” 《封锁》中讨论的是一个常态空间中人的非常态欲望。——张爱玲觉得人的欲望能在这样一个特定环境得到生长。以现实中的一次封锁给予人性真正自由的一个机会,电车象征了真正的人性世界。象征是张爱玲惯用的手法,用具体的事物表现某种特殊的意义。写小说不可太直白,否则就如凉白开水一样索然无味。在她的小说里,象征之物随处可见,象征在作品里代替她又成了她与读者交流的工具。
在小说中,张爱玲还频繁灵活运用各种意象,让人和偶像在特定的条件下高度地融合在一起,产生出新的本质已发生改变的新形象,完成了她故事叙述过程中作者的生命感悟的诗意表述。成功地使用意象的例子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俯拾皆是,可以说,现代文学史上很难找出其他任何作家像她这样在小说中运用如此繁多的意象,意象在她的小说中功用很多,如增强故事的生动性与画面感,使读者产生丰富的联想,传达人物特定的心里状态等等。这些意象都是人所习见的物象,符合日常的经验,符合规定情景,并没有奇情异趣和夸张变形,每一笔都是严格意义上的写实,然而由于她能够在意象营造上别出心裁,融入人物的主观感受及她对生命的感悟,使原本无生命的景物仿佛有了生命,获得了超越本体的象征意义,令读者能在这些习见事物构成的意象中感悟到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这些大量散布在故事进程中富有象征意味的意象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丰富了小说的意蕴,同时又将小说的题旨传达得更为含蓄、隽永,从而也使小说具有浓厚的象征色彩。
在《沉香屑 第一炉香》中,薇龙在真正进入了梁宅的生活之前,作者用意象表现了从不同时间,不同角度对这个环境的感受和体验。第一次是在白天,太阳下的景物显得清晰悦目,“姑母家里的花园不过是一个长方形的草坪,四周围绕着矮矮的白石福字栏杆,栏杆外就是一片荒山,这园子仿佛是乱山中凭空擎出的一只金漆托盘。”薇龙心中怀着的一点希望是她人生中的一个亮点;第二次是薇龙下山时回望梁宅,“薇龙站住了,歇了一会儿脚,倒有点惘然。再回头看姑妈的家,依稀还见那黄红边的窗棂,绿玻璃映着海色,那巍巍的白房子,盖着绿色的玻璃瓦,很有点像古代的皇陵。”感到一切像梦幻般不够真实,“皇陵”一词也暗示了梁宅是以年轻女孩子的青春为殉葬品的富贵繁华地;她再次看到梁宅是在有雾的晚上,“那是个潮湿的春天的晚上,香港山上的雾是最有名的。梁宅那白房子黏捻地融化在白雾里,只看见绿玻璃窗里晃动着灯光,绿幽幽的,一方一方,像薄荷酒里的冰块,渐渐地冰块也化成了水——雾浓了,窗格子里的灯光也消失了。”这栋隐在浓浓的雾气后面的宅第象征了薇龙飘渺不定的未来。在这几个极富画面感的意象中,不仅投射了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心里状态和主观感受,而且隐含着对人物不幸命运的预示。同时,作者的人生感悟也不失时机地在此逸出,一切繁华热闹都是过眼烟云,就像那只“乱山中凭空擎出的金漆托盘,”有着荒凉的背景。时代的毁灭感,生命的无常感,文明的脆弱性……这一切都使人生中可感的事物会像云雾一般消散,再美好的生命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迈进历史的坟墓。
类似这样的意象在张爱玲的小说中真是多如繁星,不胜枚举。应该说,正是这样的象征和意象使张爱玲的小说魅力永存,历久长新。
“宝石镶嵌的图画被人欣赏,并非为了宝石的彩色。”[2]但是傅雷先生的这句话也确实说出了张爱玲在其小说创作中,她的语言艺术所起到的作用。勿庸置疑,张爱玲精湛的语言技巧也是她的小说永远吸引着读者的原因。她的诡异的色彩运用和她的小说里反复出现的各种比喻象征和意象,给她的小说印上了“张爱玲”的防伪标记。张爱玲在中国文坛划破长空的出现,不但丰富了文学艺术语言的宝库,为民族语言的创造性运用提供了一个范本,也给她以后的作家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参考文献
1.夏志清 《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文联出版社1998.9出版(12)
2.傅雷 《论张爱玲的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4出版(87,94)
张洁
[摘要] 张爱玲作为一个从40年代就大红大紫的女作家,她的作品一直倍关注。她的作品被傅雷称为“我们文坛上最美的收获之一。”张爱玲的小说不仅在人性方面有深刻入微的挖掘,表现“压抑的悲哀”相当出色。更另笔者惊叹的是她的语言艺术,可谓出神入化。她的奇巧的比喻,她的诡异的色彩运用,和她的文章里反复出现的各种意象与象征,构成了她精湛的语言技巧。使得她的小说魅力永存,历久长新。
[关键词] 张爱玲;语言;比喻;色彩;意象,象征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独树一帜的、极富传奇色彩的作家,夏志清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里用了四十多页的篇幅为张爱玲正名,到现在,港台旅美作家把张爱玲的创作成就摆在鲁迅、巴金、茅盾等现代名家“等高”的位置上,把她誉为“中国最优秀、最主要的作家之一”。[1] 傅雷先生在1933年所著的《论张爱玲的小说》里曾写到“总而言之,才华最爱出卖人!像张女士般有多方面的修养而能充分运用的作家(绘画、音乐、历史的运用,使她的文章特别富丽动人)……”[2] 虽然在这里傅雷先生是在批评着新生的女作家张爱玲女士,但是实际上也是从另一个侧面间接地肯定了张爱玲作品所体现出来的文学才华。其小说的魅力,不只在于她以一支细致传神的笔精彩地描绘了殖民地香港和沦陷区上海独特的时代风情,也不只在于她那个时代,她执着于自己的世界,抒写普通人的悲欢离合,而更多的在于她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对人生悲剧性的深刻认知,以及她在作品中所表现出的独特的悲剧美。张爱玲的小说不仅在人性方面有深刻入微的挖掘,表现“压抑的悲哀”相当出色,更令笔者惊叹的是她的语言特色,可称出神入化。自从张爱玲于1944年的小说集《传奇》问世之后,便震惊世人,其作品的艺术魅力,激荡人心,特别是她小说所独具的语言更是娴熟、精湛,富有创造力,让人难以忘怀。
一、对形象独特的比喻的偏好
张爱玲是一个有着与众不同个性的作家,她看似世俗,实则超凡脱俗,这一点在她的小说中表现出来就是她对事物独树一帜的敏锐感受,最突出的便是她把这样体验独特的感受运用恰到好处,极具艺术感染力的比喻外化出来。在她的作品里,从不吝啬使用比喻,似乎万事万物皆可拿来做比喻,就连很多别人已经写过、写滥的事和物在她的笔下,也突然就与其他事物发生了联系,变成了绝妙的比喻,变成了她任意驱使表达爱憎的工具,就像她最经典的那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让人禁不住一读三叹,拊掌称妙。在《沉香屑 第一炉香》里她曾写到“薇龙那天穿着一件磁青薄绸旗袍,给他那双绿眼睛一看,她觉得她手臂像热腾腾的牛奶似的,从青色的壶里倒了出来,管也管不住,整个的自己全泼出来了。”这是一段以热牛奶比喻女人臂膊之洁白美丽的绝妙描写。在一般人的概念里,固体的手臂再白,却与液状的牛奶毫不相干,两者的差距不言而喻,只有一点“白”是相似的。写女人肌肤嫩白的比喻又何止千种万种,却从来没有人把这样的肌肤之白比作自己往外泼的牛奶。这样的描写既通过读者的视觉来让人感受乔琪的色迷心窍、蠢蠢欲动的形象,又表现了薇龙的竭力自持却又虚荣不能自拔的心态。张爱玲的话语止于此处,似乎只小小的比喻,略有点通感的意味,但是却于其中又蕴涵深幽绵远的暗示,这种暗示似无却有,把作者想说又不必说出、把读者能懂但又看不到的话不知不觉地说了出来,好像是张爱玲的不经意的一个眼神过来,就让读者随即体会了她在此细微的感觉,完成了作者与读者之间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里的交流。
张爱玲的话语不但是独特的,而且相较于其他作家而言,更近似于“恶毒”,许多通常人们以为美的事物、善的事物,在她的笔下都和我们的日常经验发生了扭转性的变化,有时让人读后瞠目结舌。似乎在她的世界里,白雪公主也有如狼外婆般丑陋的时候,但是正是这种“恶毒”的比喻,她的温和的话语更能一语中的,深刻地反映出事物的本质来。并且这样的比喻下,讽刺变得鲜明起来,幽默也将更加凸显。
张爱玲在香港读书期间,她的表姊在上海去世了。听闻这个消息,张爱玲很是悲痛,后来便有了以这个表姊为原型的小说《花凋》。《花凋》里的主人公郑川嫦的父亲郑先生的原型也就是张爱玲的舅父。可是她终究没有给自己的亲人留一点情面:“郑先生是个遗少,因为不承认民国,自从民国纪元起他就没长过岁数。虽然也知道醇酒妇人和鸦片,心还是孩子的心。他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多么恐怖的字眼,就像上层人士不说粗话一样,风雅的文人也决计不会碰触这样的字眼——也许想都无法想到。可是张爱玲这样出人意料地一一写出来,似乎就再也没有比这更贴切的字眼了。郑先生的装腔作态,他的严重的不合适宜在张爱玲残酷的比喻下,一下子现出了原型。而正是这句话,为下文打好了伏笔。郑川嫦在有生之年没有长久幸福过,连死后还要被装点成为家庭的门面,全是因为有这样的父亲,这样的家庭。这就是张爱玲语言的魔力,仅用一个辛辣的讽刺比喻,就统一了整篇小说的背景,推动了所有情节的展开。
但是让比喻之间跳跃着幽默诙谐的音符,也是张爱玲语言的特点。在《花凋》里她也戏谑幽默:“郑太太对孩子说:‘新鞋上糊了这些泥?还不到门口的棕垫子上塌掉它!’那孩子只顾把酒席上的杏仁抓来吃,不肯走开,只吹了一声口哨,把家里养的大狗唤了来,将鞋在狗背上塌来塌去,刷去了泥污。郑家这样的大黄狗有两三只,老而疏懒,身上生癣处皮毛脱落,拦门躺着,乍看就仿佛是一块敝旧的棕毛毯。”看小说看到此处的读者,虽然对于郑先生家的种种已经见惯不怪了,但是这里又突然冒出了一只可以擦鞋的狗,还是让他们不禁莞尔,书中阴沉的气氛也似乎有了亮点,郑家的一切我们也看得更加通透了。
在小说中把常见的意象和画面变得更加生动、活跃、更具风姿,生动地传递本体和喻体之间的共同神韵;把心中的丘壑附在形象的比喻中,用比喻更好地完成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和沟通;用比喻为情节造势,让读者在或惊异或放松的心态下慢慢地走进作者创造的故事中去。这,就是张爱玲的比喻,就是张爱玲的语言艺术。
二、对色彩语言的反义活用的热爱
张爱玲不仅仅是一个作家,正如傅雷先生所说,她具有多方面的才华,还可称得上是一个画家。她的作品就是由一幅幅的画组合而成,由一种种的色彩搭配而成,愉悦的场面她便给加上明快的颜色,压抑的场面她便给加上暗淡的色彩。张爱玲自己也在她的《天才梦》里写到:“对于色彩、音符、字眼我及其敏感。”“我学写文章,爱用‘色彩浓厚、音韵铿锵的字眼’如‘珠灰’、‘黄昏’、‘婉秒’,‘splendour’,’melantholy’,因此常犯了堆砌的毛病。直到现在,我仍然爱看《聊斋志异》与俗气的巴黎时装广告,便是为了这种有吸引力的字眼。”对于色彩,她有着与众不同的见解,总不按常规出牌,不按常理用词,有着鲜明的“张爱玲”特质,这也是她的一大特点。
《鸿鸾禧》里长着团白脸的已婚女人娄太太,不被家人尊重,孤独哀伤,借给未来媳妇做花鞋来解除忧虑。而新娘玉清出嫁前,竟然有一种“决绝的、悲凉的感觉”,结婚进行曲演奏时,‘半闭着眼睛的白色新娘像是复活的清晨还没有醒过来的尸首’。通常意义上穿着白色婚纱的新娘是一个女人一生中扮演的最美丽的角色,张爱玲却比之为令人作呕的毫无人色的尸首,从而前所未有地对传统意义上的纯洁白色进行了创造性的恶意运用。在这白色尸首的映衬下,小说前面大量色彩铺垫便构成了一种无意义,一种反讽。除了“白”,张爱玲的作品中也屡屡出现“红”。《红玫瑰与白玫瑰》更多次写到红色。在振保与娇蕊一夜床第之欢后,张爱玲写到“昨天晚上忘了看看有月亮没有,应当是红色的月牙。”这是虚写。另一次是实写,振保醒来后发现头发里有一弯剪下来的指甲,像小红月牙,那是娇蕊看到自己养的指甲划伤振保后剪下的。此处红色既是实写又是想象,既象征王娇蕊旺盛的生命力和热烈的情感,又有与振保偷情后的愉悦与不安。此后,张爱玲又将“红”与“白”做了一次无人能出其右的对比:“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窗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红色是蚊子血,给了人一种肮脏的感觉,是心口上的朱砂痣,却暗含了一种得不到的痛苦,由此,张爱玲又消解了传统意义上的“红”的内涵。色彩本是一种没有生命的存在,而色彩语言经过作家心灵之光的辐射和审美观照后,就已凝聚了作家的独特个性与生命追求。
在张爱玲的笔下,人生就是色彩,无数的人生就是由五颜六色,千姿百态的色彩构成的,在她的心中,色彩就是人生,色彩里包容了一切她所看到、所知道、所倾诉的百态人生。对读者而言,色彩在张爱玲的小说里不再是一种简单的语言符号,而是她对语言出神入化的把握和摆布,是她对往事、对生活、对情感、对人生、对世界的一种超越和诠释。她赋予色彩以生命,她用色彩表达了另一种情愫,也许这正是她的小说艺术产生了无穷美丽的重要原因,也正是她的小说百读不厌的原因所在。
三、对象征、意象美的执意追求
“一辆衔接一辆,像排了队的小孩,嘈杂、叫嚣,愉快地打着哑嗓子的铃:“克林,克赖,克林,克赖!”——“电车”,这个名词曾经反复出现在张爱玲的文字里:“有时候,电车全进了厂了,单剩下一辆,神秘地,像被遗弃似的,停在街心。”电车最初的意义只是一种穿行于城市的交通工具,一种载体。但在张爱玲的视野里,它逐渐升华为承载生命的容器。正是通过《封锁》的创作,张爱玲开始了对“电车”象征意义的发掘。“如果不碰到封锁,电车的进行是永远不会断的。”电车突然不再在正常的轨道上像往常一样往前走了,那么溢出正常生活轨道之后人会出现一些怎样的问题呢?华茂银行的会计师吕宗桢开始鼓起勇气向身边的吴翠远说话了,只是聊聊,就开始了诉说,慢慢的,在电车这个与外界隔绝的容器里,他开始掉进了自己织的网中,说着说着,忽然就觉得恋爱了,断定了翠远“是一个可爱的女人——白,稀薄,温热,像冬天里你自己嘴里呵出来的一口气。” 想到了他们的结合会牺牲了她的前程。可是终究,“封锁开放了。‘叮玲玲玲玲玲’摇着铃,电车载着吕宗桢回到了家里,而电车上那个女人的脸已经开始模糊,残存的印象只有自己说过的一些话。” 《封锁》中讨论的是一个常态空间中人的非常态欲望。——张爱玲觉得人的欲望能在这样一个特定环境得到生长。以现实中的一次封锁给予人性真正自由的一个机会,电车象征了真正的人性世界。象征是张爱玲惯用的手法,用具体的事物表现某种特殊的意义。写小说不可太直白,否则就如凉白开水一样索然无味。在她的小说里,象征之物随处可见,象征在作品里代替她又成了她与读者交流的工具。
在小说中,张爱玲还频繁灵活运用各种意象,让人和偶像在特定的条件下高度地融合在一起,产生出新的本质已发生改变的新形象,完成了她故事叙述过程中作者的生命感悟的诗意表述。成功地使用意象的例子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俯拾皆是,可以说,现代文学史上很难找出其他任何作家像她这样在小说中运用如此繁多的意象,意象在她的小说中功用很多,如增强故事的生动性与画面感,使读者产生丰富的联想,传达人物特定的心里状态等等。这些意象都是人所习见的物象,符合日常的经验,符合规定情景,并没有奇情异趣和夸张变形,每一笔都是严格意义上的写实,然而由于她能够在意象营造上别出心裁,融入人物的主观感受及她对生命的感悟,使原本无生命的景物仿佛有了生命,获得了超越本体的象征意义,令读者能在这些习见事物构成的意象中感悟到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这些大量散布在故事进程中富有象征意味的意象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丰富了小说的意蕴,同时又将小说的题旨传达得更为含蓄、隽永,从而也使小说具有浓厚的象征色彩。
在《沉香屑 第一炉香》中,薇龙在真正进入了梁宅的生活之前,作者用意象表现了从不同时间,不同角度对这个环境的感受和体验。第一次是在白天,太阳下的景物显得清晰悦目,“姑母家里的花园不过是一个长方形的草坪,四周围绕着矮矮的白石福字栏杆,栏杆外就是一片荒山,这园子仿佛是乱山中凭空擎出的一只金漆托盘。”薇龙心中怀着的一点希望是她人生中的一个亮点;第二次是薇龙下山时回望梁宅,“薇龙站住了,歇了一会儿脚,倒有点惘然。再回头看姑妈的家,依稀还见那黄红边的窗棂,绿玻璃映着海色,那巍巍的白房子,盖着绿色的玻璃瓦,很有点像古代的皇陵。”感到一切像梦幻般不够真实,“皇陵”一词也暗示了梁宅是以年轻女孩子的青春为殉葬品的富贵繁华地;她再次看到梁宅是在有雾的晚上,“那是个潮湿的春天的晚上,香港山上的雾是最有名的。梁宅那白房子黏捻地融化在白雾里,只看见绿玻璃窗里晃动着灯光,绿幽幽的,一方一方,像薄荷酒里的冰块,渐渐地冰块也化成了水——雾浓了,窗格子里的灯光也消失了。”这栋隐在浓浓的雾气后面的宅第象征了薇龙飘渺不定的未来。在这几个极富画面感的意象中,不仅投射了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心里状态和主观感受,而且隐含着对人物不幸命运的预示。同时,作者的人生感悟也不失时机地在此逸出,一切繁华热闹都是过眼烟云,就像那只“乱山中凭空擎出的金漆托盘,”有着荒凉的背景。时代的毁灭感,生命的无常感,文明的脆弱性……这一切都使人生中可感的事物会像云雾一般消散,再美好的生命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迈进历史的坟墓。
类似这样的意象在张爱玲的小说中真是多如繁星,不胜枚举。应该说,正是这样的象征和意象使张爱玲的小说魅力永存,历久长新。
“宝石镶嵌的图画被人欣赏,并非为了宝石的彩色。”[2]但是傅雷先生的这句话也确实说出了张爱玲在其小说创作中,她的语言艺术所起到的作用。勿庸置疑,张爱玲精湛的语言技巧也是她的小说永远吸引着读者的原因。她的诡异的色彩运用和她的小说里反复出现的各种比喻象征和意象,给她的小说印上了“张爱玲”的防伪标记。张爱玲在中国文坛划破长空的出现,不但丰富了文学艺术语言的宝库,为民族语言的创造性运用提供了一个范本,也给她以后的作家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参考文献
1.夏志清 《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文联出版社1998.9出版(12)
2.傅雷 《论张爱玲的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4出版(87,94)
温馨提示:内容为网友见解,仅供参考
第1个回答 2011-07-26
张爱玲的书看过一些,但实在悟性不足,多不理解,初中的时候当小说看过,觉得现实的可怕。大学重读,有一种悲凉到心理的感觉。像是一只是秋天,哪怕是春天,也是仄仄的。张爱玲对胡兰成说过句话,大意是,在你面前我低到尘埃里,再从尘埃里开出花朵来。
第2个回答 2011-07-25
将来是要装在水晶瓶里用双手捧着看的-----我最初也是最后的爱
最爱这句
最爱这句
相似回答